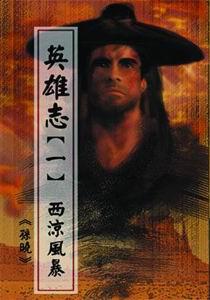在场心下雪亮,都知道这是个借口,成吉思汗压根不在乎什么商队,他只是要找个理由,遂其征服。想到塔塔儿部的前例,载志不由害怕啼哭:「那……那花剌子模的百姓要怎么办?」杨肃观道:「他们还有个寄望,那是一位很厉害的大将。」众孩童大喜道:「他是谁?」杨肃观微微一笑,转望台下,灭里明白他的心思,便点了点头,道:「杨大人所言的名将,当是后来花剌子模的一代圣君,扎兰丁。」孩童们呼吸加快,隐隐感到兴奋,都觉得花剌子模的百姓有救了。一片寂静间,只见杨肃观负手踱步,淡淡说道:「这位扎兰丁……他的才干之高,放眼当时西域,无人可出其右,乃是百年一出的豪杰。可此人又何其不幸,竟与成吉思汗生于同时,然而无论幸或不幸,当时全花剌子模的生死兴亡,全都落在他的肩上了。」「金宣宗兴定三年……」杨肃观停下脚来,手指地理图,道:「成吉思汗亲率六十万铁骑,借口花剌子模杀其商队,开拔西征,相传他的军马扑天盖地,宽达十里,长达三十里,大军抵达阿姆河畔时,花剌子模朝野震动,人人心里都明白,此战若败,则举国之男子,都将为刀下之亡魂,举国之女子,都将沦为蒙古兵卒蹂躏泄欲之玩物。亡国灭种之祸,便在眼前……」啪啪两声,把手一拍,朗声道:「诸世子!设若你是扎兰丁!你将如何救亡图存?」大哉此问,全场都静了下来,连那载志也呆若木鸡,想来是被这情势吓坏了。卢云深深吸了口气,心道:「看来这回文试,杨肃观是真心要挑一位储君了。」杨肃观用心良苦,已然设下了一道难题,马人杰、牟俊逸也都没说话了,转看银川公主,仍是一动不动,至于灭里,却已低头沈思,想来也在思索当时局势。一片寂静间,忽听那房总管道:「杨大人,难道当时花剌子模只有主战一派,没有主和之人吗?」听得呸的一声,那载碁骂道:「都打到家门口了,还有人敢主和?我要是皇帝,立时把他烹成一锅粥!」闻此纣王暴行,房总管吓得面色如土,何大人笑道:「房万年啊,这说来是你的不是了,平白无故的,干啥要求和啊?」忽听一人道:「要是打不过呢?那要不要求和?」卢云心下一凛,凝目来看,却见席间坐了一名孩童,面色蜡黄,体形瘦弱,身上朝袍居然还打着补丁。杨肃观微微一笑,道:「寿春王有何高见?」在场「徽王徐丰鲁」,加上那个小胖子,莫不是世子,却居然有位王爷?那孩童低头站起,细声道:「回杨大人的话,樉德若在当时,蒙此国难,必力排众议,力主求和。」杨肃观道:「为何如此?」那孩童低声道:「成吉思汗,向有战神之称。花剌子模不打则已,要打便得打赢他们,否则百姓必受大屠杀。依樉德之见,既然此战必败,不如先忍辱求和,若只想逞一时之快,只怕连日后复兴的机会也没有了。」牟俊逸笑道:「寿春王,你这话怎么听着听,却像是某人在论西郊战局的调子啊?」那孩童微微咳嗽,便朝马人杰看去,卢云心下一醒,已知这孩子是马人杰的徒弟,想来他是要借这孩子的口,明论花剌子模,实则暗指西郊战局。又听杨肃观道:「那照寿春王的意思,花剌子模这一战,是不能打了?」樉德道:「兵者不祥之器,圣人不得以而用之。樉德虽享王爵,却也略知百姓之苦,大战将起,征兵令一下,百姓已是流离失所,若还打个大败仗,却要置万民于何地?是以樉德若在其位,当此战神来袭,绝不敢搦其锋芒。只能先留一口气,等蓄积国力之后,方能与之较量。」看这樉德确实聪明,小小年纪便能出口成章,宛然便是个小圣君,连银川公主也凝视这孩子,想来樉德之言,已然深深打动了她。眼看太子人选呼之欲出了,忽听一人道:「杨大人,载允有话想说。」杨肃观道:「法堂上畅所欲言,世子不必客气。」载允道:「我曾听先……父王提及,成吉思汗西征前,早已打算要攻破花剌子模,将他们的百姓全数杀光。试想兵马都到了城下,岂容敌人摇尾乞怜?要想乞和,无异于缘木求鱼。」杨肃观道:「那照世子之见,该怎么做?」载允咬牙道:「生!亦我所欲也!义!亦我所欲也!今日天下大局,若想救亡图存,须得背水一战!若想灭我国土、蹂躏吾母吾姊,先得取我大汉男儿之首级!」说着说,一拳便捶上了桌,厉声道:「你要战!便作战!」这话说得慷慨激昂,真有「秦皇汉武」之志,众大臣莫不暗自心惊,载志则是叫起好来了:「载允哥好棒!娃娃这皇帝就让你当啦!」载允主战,樉德主和,一片沈寂间,人人都没说话了。忽听杨肃观道:「灭里将军,花剌子模开战后,胜负如何?」灭里道:「回杨大人的话。蒙古大军渡过阿姆河后,势如破竹,攻破玉龙桀赤后,更屠杀了百万妇孺,其状惨不忍睹。」杨肃观道:「这么说来,他们亡国了?」灭里道:「非但亡国,尚且灭种。成吉思汗掳掠后妃,当着她们的面斩杀她们的幼儿,王子们首级刚断,便又将他们的母亲尽数强奸。」听得此言,世子们或发抖、或啜泣,载允更仰起头来,嚎啕大哭。杨肃观道:「依将军看来,若是花剌子模开城投降呢?可减多少死伤?」灭里道:「开不开城,并无不同。成吉思汗乃天下第一无信之人。西征时他曾诱骗一只守军开城,入城后又杀光了全城百姓。」牟俊逸听着听,忽地笑了起来:「杨大人啊,这和也是死,战也是死,您老人家若在当时,可要怎么应变啊?」杨肃观道:「我都无所谓。」众大臣愣住了:「无所谓?」杨肃观转望台下,道:「唐王世子,你怎么说?」众人顺着他的目光去看,却见一个孩子,手拿小算盘,正自拨弄为戏,听了说话,也是不知不觉。房总管咳嗽一声,道:「载昊、载昊,杨大人和你说话哪。」叫了两声,那世子方才惊觉过来,忙道:「是……是叫我吗……」杨肃观微笑道:「是,下官想请教世子,这花剌子模与蒙古的大战,你主和还是主战?」那世子低声道:「这……我不知道啊……」杨肃观微笑道:「是和是战,人人都得选。你也不例外。」那世子低声道:「那……那好吧,我得用算盘打一打……」众人笑了起来:「是和是战,也能用算盘打?」那载昊看来很是胆小,怯怯地道:「杨大人,请您告诉载昊,蒙古兵有多少人?」杨肃观道:「号称六十万,实则三十万。」载昊拨了拨算盘,又道:「那花剌子模有多少兵马?」杨肃观道:「少说四十万,实则五十万。」看这载昊手持算盘,好似是个小小的「大掌柜」,拨了拨算珠,喜道:「这是一倍半!那我主打!」载允冷笑道:「千军易得、一将难求,大战一开,每每以少胜多,还能这般算法么?」载昊听得斥责,立时低头不语,杨肃观温言道:「不怕,我也喜欢打算盘,跟我说吧,你是不是精于珠算?」那载昊很是高兴,拼命点头:「是啊,我最能打算盘了,我父王生意做得多,每天都让我拨算珠呢,只可惜……只可惜……」杨肃观微笑道:「可惜什么?」载昊叹了口气:「只可惜要当皇帝的人,不能只会拨算盘。」杨肃观微笑道:「说得很好啊,那他该会什么?」载昊道:「他该明仁义、布礼乐、知人心。」卢云听在耳里,心下大悦,那陈二辅、房总管也是频频喝采,淑宁却是低哼一声,骂道:「铜臭!」「铜臭」二字一说,卢云心下一醒,已知这「唐王」必是家财亿万之人,想来生意做得极大,八成还做到几位大臣家里去了。杨肃观却是不以为意,含笑道:「唐王所言不错,治理天下,正在于明仁义、知人心,只不知唐王如此贤能,可曾把这仁义之术传给世子了?」载昊低声道:「这……这很难学啊,只要是算盘能打出来的,我都会,可这仁义人心看不见、摸不着,载昊就没办法了。」这话一说,人人都感莞尔,何大人哈哈笑道:「世子啊!我看你还是别想当太子啦,赶紧去户部做度支吧,老夫第一个荐保你。」载昊脸红耳赤,不敢应答,杨肃观微笑道:「世子,请恕下官直言,你的算盘没学到家。」载昊茫然道:「是吗?」杨肃观道:「是。在我看来,天下一切万物,都可以用算盘拨出来。拨不出,是你没学好。」载昊更惊讶了:「那……那这个仁义、人心,也可以用算盘算出来吗?」杨肃观含笑道:「当然了,我这一生,都在做这件事。」这话一说,卢云自是大大的不以为然,马人杰也是咳嗽连连,牟俊逸笑道:「杨大人,人算不如天算啊,那照您的意思,这花剌子模该和该战,也能用算盘打了?」杨肃观道:「我说过了,天下一切大事,都得先用算盘打一打,方明虚实。」牟俊逸笑道:「怎么打法?拿算盘砸人?」正要哈哈大笑,却听杨肃观道:「牟大人,这和战之间,本是一体之两面。蒙古所欲谋我者,不过食粮、美女、金帛三者,我若杀美女、焚金帛、毁食粮,试问蒙古跋涉万里,所为何来?死伤数十万将士,得空城一座,无功而返,我看成吉思汗怕连自己的位子都保不住了,敢问开战之前,他这算盘拨还是不拨?」听得杨肃观要坚壁清野,众人自都哑口无言了。何大人干笑道:「杨大人,这成吉思汗还没来,你自己就烧房子了?这可不大好吧?」牟俊逸也道:「正是如此,你别顾左右而言它,杨大人,敌人都打到了城下,到底是和是战,你只能选一边。」牟俊逸把话挑明了,今日局势,杨肃观究竟主战主和,他必须选。良久良久,何大人咳嗽一声,道:「杨五辅,快说吧,内阁还等着听你的高见。」何大人毕竟是当朝宰辅,非同小可,此话一说,杨肃观欠身便道:「回阁老的话,下官以为,和战必须并用。若无求战之心,便无求和可能。若无谋和之心,则战端一起,终将必败。」说着望向了那个「樉德」,道:「寿春王,您是马人杰的得意门生,您说这话是么?」那樉德甚是聪明,忙道:「杨大人教诲的是。求和一事,须得两家有心,否则单若一厢情愿,必然贻误战机。」杨肃观此话一说,又有战、又有和,看似什么都没说,可卢云却已听出了弦外之音,已知他有意以战逼和,可秦仲海岂是善男信女,倘若也抱同此心,两边把算盘一打,恐怕便打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了。一片沉默间,忽听一名孩童道:「杨大人!有件事载懹不懂!想向您请教!」牟俊逸笑道:「丰王世子有话说了。」一名孩童站起,双眼炯炯,呼吸沈缓,这孩子竟是身怀内力,何大人干笑道:「载懹,听说你练成了武当的松鹤心经,武功很了得啊。」那孩童忙道:「不敢,在座兄长都是各派师傅的高徒,载懹万万不是兄长们的敌手。」牟俊逸笑道:「做人也别太谦了。来来来,你有什么高见,这便说吧,牟叔叔替你撑腰。」这载懹正是「丰王世子」,拜了武当元易道长为师,看来武功真是冠于全场。听他朗声道:「载懹无知,方才听杨大人说,这花剌子模本有五十万兵,人数比蒙古还多,可双方决战,却怎会打不赢呢?这不是很奇怪吗?」世子们都看到了要紧处,纷纷嚷了起来:「是啊!明明人多,怎么会打不赢呢?没道理啊!」杨肃观道:「灭里将军,你看花剌子模此战为何而败?」灭里道:「其一,阵法有误。当时花剌子模君主摩诃末怯懦,成吉思汗兵临城下,他非但躲于阿姆河之后,甚且将兵力分散于各城池,故而让成吉思汗从容渡河、各个击破。」杨肃观道:「其二呢?」灭里道:「摩诃末大败之后,不思围剿反制,反而向西逃窜,直至吓死在里海为止。至他死后,扎兰丁方才向蒙古反击,可惜那时手下兵马仅剩数万人了。」众人痛心扼腕,无不暗骂昏君误国,杨肃观又道:「那若是一开始便由扎兰丁统帅,他将如何迎战蒙古大军?」灭里道:「依史书所载,扎兰丁力主决战,誓将集举国一切兵力,渡阿姆河,与成吉思汗决一死战。」载允、载碁纷纷喝采,大声道:「正该如此!」杨肃观见这两个孩子振奋激昂,便道:「徽王世子,依你之见,这阿姆河也是该越过去的?」载允大声道:「回杨大人!这河当然该过!」杨肃观道:「兵法有言,渡河未济,击其中流,你不想躲在阿姆河后,以逸待劳?」载允凛然道:「杨大人!蒙古军疾如风火,来去神速,此乃我父亲自教诲,这阿姆河更是长达数百里,蒙古军今日在东、明日在西,兵行如电,什么以逸待劳、什么截击中流,遇上蒙古兵马,都不过是书生之见罢了!」这载允是徽王爷之子,果然从小能知军国,说得竟是头头是道。杨肃观颔首道:「那越河之后呢?若由你指挥,该当如何?」载允咬牙道:「项羽破釜沈舟,韩信背水一战,皆是置死地而后生,此战若起,载允将备妥遗书,以背水之势,王见王、帅见帅,以五十万对他的三十万,寻敌死战!」载碁大吼道:「说得好!载允!咱俩一齐去杀光他们!操他的种!灭他的国!」房总管咳嗽道:「两位世子,庙堂之上,凡那几个不雅的字,都不可说。」众大臣听着载允之言,虽说大胆,倒也不是不可行,想来当初若依扎兰丁之见,花剌子模未必灭亡。良久良久,听得载允道:「杨大人,你以为载允所言如何?」杨肃观微笑道:「你很好,不过该让别人说了。」拍了拍手,道:「徐王世子,你的伤势如何了?可以说话了么?」那载儆早就醒了,只在那儿哈欠,一听此言,忙道:「我……我的头还疼着。」淑宁也低声道:「表哥,他都伤成这样了,你……你就别为难他了……」牟俊逸笑道:「庙堂之上,表哥表妹相见欢,好亲热啊。」淑宁狠狠回瞪一眼,骂道:「小人!」场面难看,只怕要吵架了。杨肃观笑了笑,道:「也罢,今晚还有谁没说过话?」小胖子喊道:「载志还没说!」杨肃观笑道:「也好,川王世子是国丈荐保的,必有高见。你说吧,你若是扎兰丁,你要怎么打成吉思汗?」小胖子咦了一声,茫然道:「谁是扎兰丁啊?」众人都笑了出来,看这载允果敢好胜,像个秦皇,载碁暴劣粗直,像个纣王,没想还多了个晋惠帝,杨肃观又道:「来,康王世子勋毅,你整夜不发一语,是不是该说些什么了?」众人一齐转过头去,望向了一名孩子,想来便是这「康王世子」了。杨肃观又道:「勋毅,你是宗人府力荐的贤能之士,说你熟读兵史,聪明过人,岂难道并无高见?」那孩子低头默然,仍旧不发一语,只是看他肤色白皙,与载允、载志等人大不相同,倒与杨肃观有三分神似,都有些王莽的影子。良久良久,那勋毅道:「回杨大人的话,这阿姆河渡是不渡,其实并无分别,照勋毅之见,此战一样必败。」载允怒道:「无知小儿!你有何凭据,敢说这话?」勋毅道:「敢问杨大人,蒙古兴起之前,天下最强的铁骑兵,由哪一国统属?」杨肃观本是监考官,没想反让人考了,当下微微一笑,便也答道:「据黄金史所载,世间第一精锐骑兵,便是大金国铁骑。」勋毅又道:「那我再请教杨大人,设若将大金国铁骑与花剌子模步兵相比,却是谁强谁弱?」杨肃观道:「自古东强西弱。大金远胜花剌字模。」勋毅道:「这就是了,敢问野狐岭之战,女真夹击蒙古,共享多少重甲骑兵?」杨肃观道:「号称六十万,实则四十万。」勋毅道:「蒙古军有多少?」杨肃观道:「号称二十万,实则不到十万。」勋毅道:「是了,我这儿再请教杨大人,当初大金对蒙古,双方以骑兵对骑兵,以四十万打十万,敢问此战之后,是谁胜了?」杨肃观笑了笑,并未回话,卢云、灭里等人却是心知肚明,均知野狐岭大战,实为女真亡国的关键一役,此战大金铁骑以数倍兵力包抄,却落得死伤大半,从此天下再无一国可独力对抗蒙古,举世皆暴露于蒙古鬼卒的斩刀之下。依此看来,扎兰丁即便率军渡河,与蒙古径行决战,只怕亦难逃覆灭下场。杨肃观道:「那照康王世子看来,摩诃末躲于城中,其实是条上策了?」勋毅道:「蒙古骑兵最善野战,以女真的六十万重装铁骑,尚且不堪一击,何况其它?摩诃末不敢野战,正是其高明之处,故而入城自保,坚守不出。说来这条计策并没有错。错只是错在他没料到蒙古人已有大炮,可怜他的城墙不够厚,只能在铁木真的面前倒下了。」全场闻言默然,均知上天不仁、必将亡花剌子模。无论扎兰丁渡不渡河、蒙古的这柄屠刀仍将斩来,恐怕韩信、项羽复生,也保不住花剌子模的举国妇孺。牟俊逸、马人杰都叹了一声,想来也没话说了,何大人低声道:「杨大人,我看时候也差不多了,咱们也该……」「大家都坐着。」杨肃观拿起茶杯,朝砚台里倒了倒水,道:「诸位,杨某留世子下来,是要告诉他们,如何才能打赢这一仗。」何大人闻言一征:「你是说……你能保住花剌子模?」杨肃观低头研墨,润了润笔,轻声道:「岂但保住花剌子模?杨某若生于西域当时,成吉思汗若敢来犯,我将亡他蒙古种姓,使其从此不复在。」牟俊逸笑道:「杨大人别要空口说白话啊。你若有这般兵法本事,何不请伍定远让贤,由你杨肃观上去?」杨肃观微笑道:「牟大人这是为难我了,杨某其实不懂兵法,也没带过兵。」牟俊逸笑道:「那杨大人夸夸其词,所为何来?你凭什么与蒙古战神相抗?」杨肃观提起白纸,拿着浆糊刷了刷,贴到了墙上,随即提起笔来,写落了两个字,道:「凭这个。」墙上多了两字楷书,端正严谨,众人凝目一看,齐声道:「正道?」相顾愕然间,只见杨肃观放落了笔,道:「诸君,何谓正道?正道者,就是做对的事。」牟俊逸呆了片刻,实在忍俊不禁、终于捧腹大笑起来:「杨大人,你也配谈正道了?那天下婊子不都能给自己立牌坊啦,哈哈!你打算拿这个笑死成吉思汗啊?」杨肃观润了润笔,在「正」字之旁添了几笔,见是个「文」字,却成了一个「政」字。众人呆呆看着,齐声道:「政道!」杨肃观放落了笔,颔首道:「这个政道,就是杨某毕生的道统。亦是灭蒙古、击战神,抗击世间一切外力的必胜之道。」银川公主原本默默无言,此时忽然抬起头来,轻轻地道:「杨大人,何谓政道?」杨肃观环顾堂下,道:「政者、正也。子率以正,孰敢不正?这个政道,其实也就是正道,然诸位可曾想过,古人造这个『政』字之时……」手指提起,定向墙上那个「政」字,道:「为何要多加一个『文』字边?」牟俊逸冷笑道:「拿着正字作文章啦。」杨肃观微笑道:「说得好。正道者,所行皆为对的事。政道者,所言必是对的事。这个『言』字呢,便是要让你打从心里相信,我所作所为的这一切……」行下台来,俯身望向牟俊逸,握住了他的手,静静地道:「都是对的事情。」牟俊逸哼了一声,别开头去,这回却也没再讥嘲了。一旁何大人干笑道:「杨大人,你靠着这个『政道』,便能挽救花剌子模吗?」杨肃观道:「这个自然。打一开始,花剌子模就用不了扎兰丁,甚且也用不了摩诃末,哪怕再多的贤臣勇将,也无法挽救当时危亡。说来世间能救花剌子模的,也只有这个『政道』。」众人愕然道:「为何如此?」杨肃观伸出手来,指了指那个「政」字,道:「诸世子,欲知一国之兴衰,必先观何处?」载昊道:「必先观钱粮。」樉德道:「必先观百姓。」载允道:「必先观军马。」小胖子狂喊道:「必先看神仙姊姊漂不漂亮!」杨肃观道:「勋毅有大才,你说吧,欲知一国之兴亡,必先观何处?」那勋毅道:「观一物,必先观其内。」杨肃观道:「何为一国之内?」勋毅道:「为百姓。」杨肃观道:「何为百姓之内?」勋毅道:「为法制风气。」杨肃观道:「很好,那法制风气之内呢?」勋毅沈吟不语,马人杰便道:「天下之风气,必起于天子。」杨肃观道:「是了,那天子之内呢?还有什么?」牟俊逸冷笑道:「私心。」杨肃观哈哈笑道:「俊逸兄大材。天子之内有私心。可牟大人怎不说说,天子的私心都藏于何处?」牟俊逸咳嗽几声,并不回话,杨肃观笑道:「难得世子都在这儿,牟大人不说,那杨某说。这帝王私心之所在,便在后宫。那儿有他最心爱的人,故而在他心中的份量,足与天下等值。」这话已然影射时政,自是谁也没接口。良久良久,忽听马人杰道:「若是皇帝并无所爱之人呢?」杨肃观道:「那他就不懂得爱任何人。他的私心会是古往今来、天下最重。」杨肃观笑了笑,望向了银川公主,又朝诸大臣瞧了瞧,道:「所以杨某观花剌子模之国政,第一件事不是看它的府库存粮,也不是看它的百姓风气,而是看摩诃末的后宫,看看他的私心何在,看看有谁可以分掉他的权。」灭里啊了一声:「你……你说得是秃儿哈干太后!」杨肃观道:「就是她。扎兰丁下野,是太后致之,摩诃末无能,是太后令之,然太后虽为弱女子,亦可能有英明处,何以言为病灶?其实这个病,不是病在她这个人,而是病在这件事,她抓了权,却不肯担责。她不担责,却又抓了权。故而有责者无权、有权者无责,做错事不知痛,便如行尸走肉,故曰花剌子模已死。」牟俊逸冷笑一声:「杨大人,你想治痼疾,蒙古大军却已在城外,这远水救不了近火,你若是扎兰丁,你要如何应付?」杨肃观道:「我若是扎兰丁,将自率国中三千美女、献一切宫内金帛,俯爬匐匐,出城跪降,以求保存举国之实力。」牟俊逸道:「若成吉思汗杀你呢?」杨肃观道:「那便死吧,王子出城乞降,尚且被杀,则举国上下谁敢再言降?王亲贵族一旦心不存侥幸,势将万众一心,起而抗之。成吉思汗若不死于西域,是为侥幸。我见国家保存、百姓俱在,虽死犹生矣。」马人杰道:「若成吉思汗放你生路,可不久又来需索,你将如何应付?」杨肃观道:「我若能逃过死劫,入城后便将政变。」众人大惊道:「政变?」杨肃观道:「是,我将幽禁太后,罢黜可汗,尽杀举国异心之人。三年之内,我将血洗蒙古,使全漠北闻吾之名,如婴儿之闻猛虎,嚎啕悲泣于万古,以昭天下之大信。」听得杨肃观公然谈论政变,何大人、房总管、诸大臣,人人面面相觑,深感此言之大逆悖乱,已臻于极。牟俊逸低声冷笑:「杨大人,你……你真想造反啦你?」杨肃观淡淡地道:「有些事,我不单是说过,还已经做过。请你们牢牢记得,杨某的政道,所言必是对的事。」说着朝八王世子欠身:「诸世子在上。臣甘冒天下之大不讳,直言上奏、句句肺腑实言,尔等若能谨记在心,则……」说着说,便摘下了「政道」二字,露出后头的黄榜,正是那七个大字:「天之历数在尔躬」。一片静默间,杨肃观收拾了东西,步下高台,随即把殿门推了开来,但见狂风暴雪扑进殿里,杨肃观微一仰首,便已迈步行了出去。杨大人前脚一走,世子们跑的跑、玩的玩,有的哈欠连连,有的睡得打呼,更有小胖子偷看美女的。一片吵嚷间,银川霍地起身,便也尾随而去,灭里急急追上,喊道:「殿下!等等!」房总管苦笑几声,眼看杨肃观走了,当下行到殿门,大喊道:「文较已毕!诸王亲随,入场接驾!」喊声一出,殿外满是叫喊:「载昊啊!考得好不好呀?」、「载儆!父王来接你啦!」堂上热闹吵杂,只见徐王、唐王亲来探望,鲁王、康王则由王妃到场,那峨眉掌门严松也在人群中,看他个子高,望来极为显眼,只在载允耳边说话。转眼之间,诸世子走的走、散的散,已是一个不剩,众大臣却还坐在那儿,陈二辅苦笑道:「这杨大人非得语不惊人死不休?这当口说这种话,真想把咱们几个都拖下水啦?」何大人低声道:「老夫先把话说清楚啦,今晚的事,谁都别望皇上那儿告状,我可不想惹麻烦。」牟俊逸骂道:「怕什么?这小子料定咱们不敢告!我偏要告!」马人杰叹道:「都别说了,走吧。」提起了拐杖,向地力撑,便也一拐一拐的离开。大风雪之中,堂外慢慢站起了一人,抖落了满身白雪,正是卢云。他朝掌中呵了口暖气,转头去看殿前广场,那杨肃观的身子已成了小小一个黑点,快要看不到了。[记住网址.三五中文网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