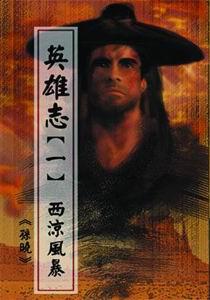“天哪!这…这究竟是…”老捕快眯着眼,抖着手,看着眼前令人恐惧至极的景象,炙热的艳阳晒下,把他微驼的背烤得火烫,但此刻的他,已被满身的冷汗浸湿,感不到丝毫暖和。他腹中传来一阵搅动,立时让他呕出淅沥沥的黄水。忽然背后一阵阴风吹来,只吓得老捕快高高跳起,他不及抹去嘴角上的秽物,连忙冲向坐骑,猛地翻身上马,尖叫道:“走!快走!”他举鞭挥下,用力在马臀上一抽,马儿吃痛,霎时一声嘶鸣,啼声隆隆中,已然飞驰而去,只见大漠中滚起漫天烟尘,远远望去,有若一条黄龙。眼见马儿奔驰奇速,老捕快还嫌不足,一阵阵无情抽打,只求早些离开这个令人恐惧至极的所在,一人一马,如同逃难般的飞奔而去。老捕快死抓着马背,喃喃自语道:“伍大爷,眼下只有靠你了…”快马奔驰着,蹄子踏在滚烫的黄沙上,像怕疼般的高高跃起,老捕快喘着气,紧绷着满是皱纹的老脸,他不住回头,似怕后头有什么怪物追来,紧握刀柄的掌心满是汗水。快马奔入了城内,眼见无数行人挡道,老捕快喝道:“让开了!让开了!”一旁百姓见快马冲来,都是急忙闪避,有的更是滚在道旁。众人见官差如此急迫,居然驾马入城,一时议论纷纷,不知发生了何等大事。老捕快一路大呼小叫,吆喝连连,接连冲过了几条大道,霎时眼前现出了一座高耸的朱红大门,门上高悬雪亮明镜。老捕快眯着满脸的皱纹,终于安下了心,因为浩然正气便在眼前,只要回到此处,便是天大的事也不怕了。此处正是西凉城的衙门,维系西疆公理的所在!“伍大爷呢?快请伍大爷!”老李声嘶力竭的吼着。一旁十多名差人正围了一圈赌牌九,满脸的疲懒油条,一个个没好气的骂道:“老李,你奶奶的嚷个什么劲儿!是不是老糊涂了?”“他妈的,老子输得正多,你这般大喊大叫,大伙儿还赌个屁啊!”另一人獐头鼠目,看起来像个小偷,嘻嘻哈哈的笑道:“老李你急什么啊?茅厕在后头,你找错地方了。”众捕快一同哄堂大笑。老李叹了一口气,这就是衙门,办案赌命、闲暇赌钱的好地方。老李任由大家笑骂着,他不会生气,他不是那种假正经的人,只是不巧得很,今日给他遇到了正经事。官差们正自嬉闹,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院外传来:“老李,出了什么事?”众人脸色一变,赶忙收拾赌具,一个个站起身子,互相扮了个鬼脸。一条大汉不疾不徐地走进院中,黝黑的四方脸上一派威严,一望便知是这些官差的头儿,衙门的捕头。老李看到大汉,露出欣慰的神情,显然这条大汉在他心中有着顶重的份量。老李急急的说道:“伍爷,城西出了事,您老赶紧去看看。”声音急躁,一点也不像上了年纪的人。一旁的官差笑道:“什么大事要劳动伍爷亲自出马?你干了这么多年的差事,难道自己还料理不了吗?”老李抹了抹汗,嘶哑着嗓门道:“这案子非同小可,伍爷可得亲自走这一趟。”一旁多嘴油舌的官差嘻嘻笑笑,还待要说,大汉哼了一声,朝那几名聚赌的人瞪了一眼,对老李说道:“可是出了人命?”他见老李点头,猛地双目一翻,沉声道:“尸首呢?”老李道:“回伍爷的话,尸首还在城西。”一名官差忍不住插口道:“你搞什么,把尸首运回来不就得了,大热天的,非要叫伍爷跑这么一趟!”老李面露苦笑,说道:“我哪搬的了这许多,死了十来个人哪!”此言一出,众人大吃一惊,那大汉双目精光暴射,霍地站起身来,大声道:“弟兄们!带好家伙,这就上路!”众官差前呼后拥,奔出衙门,那大汉领着众人飞驰而去,十余匹马一字排开,气势倒也不凡。一众官差奔出数里,行到一处小丘,老李忽尔勒马停下,众人便也一齐停步。那大汉见老李面带惊恐之色,当即问道:“尸首在这儿?”老李微微点头,嘶哑地道:“对…就…就在小丘上。”那大汉见他神色颇为恐惧,便自留上了心,问道:“怎么,那沙丘真有什么古怪?”这老李是衙门中的老手,倘若此处真有什么物事吓唬住他,料来定是非同小可。眼看老李连连点头,两名年轻官差不禁哈哈大笑,道:“老李真个没用了,活了这么大把岁数,居然还怕东怕西!”这两个人年轻好事,丝毫无惧,当下提缰夹马,便已朝丘上冲去。老李见这二人莽撞,便要将他们唤住,但又怕旁人讪笑,只有苦苦忍住。那大汉看了老李一眼,道:“有我在此处,没什么好担忧的,咱们走吧!”当下率着众官差驾马前行,老李苦着脸,却也只有随着前去。众人正要上丘,忽听丘上传来几声惊呼,那大汉心下一凛,知道上头真有什么古怪,忙喝道:“大家抽家伙,一齐上去!”众官差吃了一惊,急急拔刀,十余骑猛地飞驰而上。那大汉一马当先,率先冲到丘上,猛见先前上去的几名下属呆呆地站立不动。那大汉喝道,“怎么了?发生什么事?”那两名官差呆呆的不言不动,只是浑身颤抖,那大汉随他们的目光向前望去,顿时之间,心头也是一震。后头十来骑纷纷奔上,原本叽叽聒聒的,待见了眼前的景象,霎时也都吃惊出声。一时之间,沙丘上竟无一人说话言语,只余潇潇风声呼啸而过。漫天风砂之中,一只旗杆儿倒插在地,只留下光秃秃的大半截在外,十数具无名尸首七零八落地散在旗杆儿四处,有的蜷缩成一团,有的平躺在地,只是每具尸首的神情都惊恐异常,双眼睁得老大,好似死前见到什么可怕的景象。远处杆儿旁翻了辆骡车,已然断成两截,车里的物事四处散落,更显得无比凌乱。一名官差身子飕飕发抖,数着尸首,颤声道: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这…老天爷啊,死…死了十八个人哪!”那大汉咳了一声,定下神来,问道:“谁第一个见到这些尸体的?”老李咳了一声,道:“是一家三口见到的。这家人来西凉做些小买卖,刚巧路经此处,没想撞上了这桩血案。”那大汉嗯了一声,问道:“他们人呢?”老李道:“这一家三口给这些尸首吓坏了,现下给属下安顿在城里。”尸首全是男性,一十八名汉子惨死在地,即使在西凉这种盗匪出没的地方,这也是一起难以想见的大血案。那大汉点了点头,凝视着现场,过了半晌,他忽地咦了一声,跟着深深吸了口气,道:“不对,这里有些不对头。”众官差听他如此说话,忍不住暗暗一凛,纷纷凝目望去,却不见有什么不妥。众人摸着脑袋,都看不出所以然来。那大汉沉声道:“你们看清楚了,地下没有血迹。”众官差细细看去,赫然一惊,颤声道:“真…真的,死了十八个人,地下居然没有血迹,这…这是怎么回事?”说来奇怪,尸首横七竖八的倒了满地,地下居然没有一点血迹,这起案子看来不像是凶杀,反倒像是厉鬼索命一般,众官差望着死者惊恐万状的神情,心下都是暗自害怕。时近黄昏,远处传来乌鸦嘎嘎的叫声,更使现场蒙上诡异至极的气氛。那大汉见众人呆呆站立,都似傻了,忍不住摇了摇头,道:“大伙儿别发呆了,快干活吧!”他见众人兀自战栗害怕,便自行上前察看尸首。他见一具尸体颇为壮硕,当即蹲下检视。只见那死者身穿短衣,满脸虬髯,有些像是江湖中人,当下解开死者的衣衫,察看半天,却没看到任何外伤,实在查不出死因。老李蹲在身旁,低声问道:“到底怎么回事,怎么没半点外伤,顷刻间便死得一干二净?难道…难道这些人是生了什么急病么?”他话一出口,自己便知不对。即便是世间最恶毒的猛疾,也不能同时害死十八人,还让他们如此措手不及,看来定是另有缘故。那大汉皱着眉头,心下也感奇怪,正看间,一旁走来名官差,手上捧着一柄钢刀,低声向大汉道:“伍爷,这刀是从现场找出来的。不知是不是凶刀。”那大汉嗯了一声,急急接过刀来察看,只见那柄刀沉甸甸的,上头刻着花纹,看来颇为贵重,当是使刀名家的惯用兵刃,昏黄的夕阳映照,染得刀身血色鲜红,但上头却不曾沾染一点血迹。老李问道:“这柄刀可是歹人留下来的?”那大汉看了手上的钢刀几眼,忽又俯下身去,往那尸体的手掌一摸,霎时嘿嘿一笑,摇头道:“不,这柄刀是苦主自卫的佩刀。”老李面露讶异,怔怔地看着大汉,不知他何出此言,那大汉见老李瞠目结舌,便蹲下身来,抓起一名死者的右掌,道:“你们听好了,这些遇害的人不是寻常人,全都是武林好手。”此言一出,众人更是诧异。那大汉知道众人不信,当即道:“你们过来看看这人的手掌。”众人依言走上,只见死者的手指有些异样,关节处异常鼓胀,掌上更是生满了老茧,看来极为怪异。那大汉沉声道:“看出啥了么?”眼见众人摇了摇头,那大汉道:“寻常人日子不管怎么辛苦,便是干挑夫的苦力,手掌至多生些硬茧,绝不会变成这等模样,惟有苦练过铁砂掌的外门高手,双手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些死者的身分不寻常。”众官差骇然出声,方知这些人真是武林好手,老李惊道:“他们真是武林人物?那他们是打哪儿来的,又是谁杀了他们?”那大汉不答,只沉吟片刻,转身便朝旗杆儿走去,那旗杆倒插在地,旗面已然隐入沙中,只余光溜溜的旗杆露在外头。那大汉紧皱眉头,迳自拔起旗杆,一阵狂风吹来,那大旗迎风展开,上头赫然现出四个大字:“燕陵镖局!”老李一见那四字,登时倒退两步,颤声道:“伍爷!是燕陵镖局!是燕陵镖局!”那大汉干笑一声,嘶哑地道:“没错,正是燕陵镖局。”他回头望去,只见众官差脸上一齐变色,一时面面相觑,都是惊惧不定。老李骇然道:“伍…伍爷,怎么会这样…杀人不见血,干掉的还是燕陵镖局的好手,这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…”一名年老的官差喃喃地道:“这是鬼…是鬼…要不是鬼,怎么会杀人不见血…”众人听到这话,都是倒抽一口冷气。几个年轻识浅的小伙子,更是吓得挤在一起,飕飕发抖。现场风声萧萧,有如鬼哭,一十八具不明死因的尸首僵直在地,还都张着灰暗的双目,好似随时会跳跃起来似的,众人心中害怕,一步步地向后退开,远处夕阳斜斜照来,把各人惨白的脸都给染得血红了。那大汉环视众人,只见属下个个心惊胆跳,还不住地往后退,几名年老官差口中念佛,更增惊扰。那大汉怒气上涌,大喝一声,怒道:“全都给我住嘴了!”众官差吓了一跳,连忙噤声,无人敢发一言。那大汉怒视众人,跟着刷地一声,拔出佩刀,朗声道:“你们听仔细了!有我西凉伍定远在此,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!管他是人是兽,是鬼是怪,只要敢胆在西凉犯下人命,姓伍的照样要拿它归案!”夕阳斜照,那大汉手持钢刀,仰天傲视,一股说不出的英雄气魄,油然而生。这起案子来势汹汹,可说是西凉数十年来罕见的重案,却也遇着了正主儿。这大汉不是别人,正是西凉一带威名素着的捕快伍定远,今年三十有五,上任六年来,仗着办案心细,武艺精熟,早已办下十数桩大案,一只“飞天银梭”更是名震西凉黑白两道,算得是西凉难得的人才。此时伍定远语声激昂,扬刀立约,众官差都是精神一振。伍定远提声喝道:“小金!快请黄老仵作!”那小金闻言惊道:“黄老师傅早就洗手退隐啦,真要惊动他老人家吗?”伍定远解下腰上令牌,沉声道:“你立刻带了我的令牌,速请黄老师傅走一趟。此事万万不可张扬,暂且别让燕陵镖局得知此事!”小金不敢多说什么,上马而去。伍定远哼地一声,说道:“好小子,哪来这许多练家子,原来都是燕陵的倘子手。”众人兀自惊疑不定,没人敢接话,老李走上两步,低声道:“这燕陵镖局势力雄强,数十年来不曾出过事,怎会有人敢在老虎嘴上拔毛,却来干翻燕陵的镖师?莫非失心疯了?”伍定远冷笑一声,道:“谁晓得,这些强人见钱眼开,一给他们见到白花花的银子,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”江湖上铤而走险的凶狠之辈,所在多有,伍定远是看得多了。有些财迷心窍,好容易开了间客店,却从来不干正经营生,整日只会下蒙汗药害那往来客商的,他也破获多起。想来燕陵镖局树大招风,经手运送的都是白花花的官银、亮晶晶的珠宝,难怪江湖上的小贼眼红,只要见了好处,怕连性命也不要了。老李问道:“到底这案子是什么人干下的,不知伍爷心中可有个底?”伍定远微一沉吟,道:“这我也说不准,往日办案,多少都可以从尸首上查起,只是这十八名镖师的死因太过奇怪,个个身无外伤,实在看不出从下手之人的武功家数。只有等黄老忤作到了,才能说个明白。”老李道:“放眼西凉,只怕没人有本领一次做翻燕陵镖局的十八名好手,我看歹人定是下毒谋害,使得是蒙汗药、迷魂酒这类的伎俩。”伍定远点头道:“当是如此。”伍定远在西凉也算是个成名好手,但以他的武功家底,尚且不能一举做翻十八名镖师,何况他人?想来歹徒若非在食物中掺毒,便是用细小暗器暗算,否则如何对付得了这许多硬手。他召来众人,细细吩咐道:“死者既是镖局的倘子手,必是运送些价值连城的宝贝,你们去查查他们运的是什么物事,把失落的财物都点清楚了。”一众手下答应一声,急急前去搜索,伍定远却自行走开,心下不住推算计较,说来这案子并不难破,只要能查出这些尸首的真正死因,定能找出下手之人,在这荒荒大漠之中,这群人便想藏身,却也无处可去。到时无论歹徒是何方神圣,只要派出大批官差,全力围捕追杀,定可将他们手到擒来。这案子并不为难,让他烦心的只有一个人,一个惹不起的麻烦苦主,燕陵镖局的齐润翔。伍定远轻叹一声,他走向前去,找块大石坐下,远远眺望沙漠的夕阳,心中不住盘算。想那燕陵镖局开立至今,已有数十年历史,向来是硬底子的老字号。总镖头齐润翔武功高超,仗着江湖朋友众多,向不和官府交往,伍定远干这捕快也有六、七年了,始终没和他来往。饶是如此,燕陵镖局却不曾作奸犯科,只是本本分分地做生意,伍定远也乐得和齐润翔井水不犯河水,老死不相往来。原本大家太太平平过日子,岂不是好?谁知燕陵镖局不出事则已,一出事就是大案子,连着死了十八个人,这齐润翔是个要面子的人,想他的局子遇上了这等大事,岂能不私下查访,报仇雪恨?怕就怕他自行动手,到时杀人放火起来,非闹得天下大乱不可,届时西凉城私相斗殴,血流成河,却要他这个捕头的脸面往哪搁去。那老李也是个老江湖了,他见伍定远烦恼,知道他在担忧燕陵镖局私下寻仇,当下道:“伍爷,待会儿验完尸,咱们便上燕陵镖局走一遭,想那齐总镖头不会不给咱们面子,事情便不难办了。”伍定远摇头道:“这齐润翔是条老狐狸,怕就怕他嘴上一套,手里一套,咱们得了面子,却要掉了里子。”两人说话间,几名官差急急奔来,禀道:“启禀伍爷,这些是死者身上发现的东西!”说着呈上几件物事,伍定远低头看去,只见属下们手上拿着一袋白银,另一人手上捧着些珠宝,伍定远挑起一枚指环,细细察看,只见这指环色泽非凡,应是上品。一名官差道:“这玩意儿是汉玉指环,玉质温润,晶莹剔透,少说值得上百两银子,凶手却弃之不顾,真是奇怪。”伍定远问道:“这戒指是在哪发现的?可是在镖局运送的箱子里找到的?”那官差道:“这倒不是,这只戒指是从死者身上除下来的。”老李大为讶异,奇道:“凶手连这样的好东西也不要,真是怪了。”伍定远沉吟道:“看来镖局运送的那几只箱子才是正主儿,里头的东西必是价值连城的珍宝吧!”那官差摇头道:“属下仔细查过,箱子里只有一些衣裳,不太像是值钱的东西。”老李一怔,道:“只有一些衣裳?这是搞什么,怎会有人托镖局来押运衣裳?”以燕陵镖局的行情身段,倘若没有千两银子,只怕很难叫他们出镖,却怎能有人付此重酬,却要镖局护送这等不值钱的东西?天下确实没有这种生意。伍定远与老李对望一眼,两人都见到彼此眼中的疑惑,二人连忙走向前去,察看镖局运送的物事。只见骡车翻覆在地,一旁翻落着几只铁箱子,共有三只之多。伍定远蹲下身去,拾起地上的一只铁锁,那锁已被撬开,早断成了两截,一旁官差道:“这几只箱子上本来是镶着锁的,全给人用重手法撬开了。”伍定远转头看去,只见满地都是衣物,四处散落,众官差正在整理,一名官差禀告道:“那些衣物都是给歹徒丢在地下的,我们适才点过,全都是些寻常事物,实在没什么值钱东西。要说歹人拿走了什么,我们也看不出来。”伍定远拾起地上的一件锦袍,料子用的是山东大绸,虽然裁剪精细,质料颇佳,但也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,反而远不及镖师身上的珠宝值钱,实在不知歹徒何以要翻搜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,却反而对珍异珠宝弃若蔽履?他苦苦思索,猜想不透这些盗贼的用意。老李苦笑道:“伍爷啊,这群凶手到底图的是什么玩意儿,您可瞧出来了吗?”伍定远摇了摇头,说道:“不管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,全都无所谓了。只要找出真凶,绳之以法,还怕追不回东西吗?”一旁几个官差见他出语豪壮,原本担心受怕,心中都是一宽,一人大声说道:“伍爷说得对!这几年来哪件案子您没给办妥过?这次虽然是燕陵镖局出事,凭伍爷的手段,那几个凶徒还逃得掉吗?”一人道:“正是!只要伍爷出马,那些贼子还不抱头鼠窜吗?”伍定远听着属下阿谀,心中却无丝毫快意,他摇头道:“大伙儿听好了,这次的案子很有些不同,咱们可得小心在意。”众官差一齐道:“还请伍爷示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