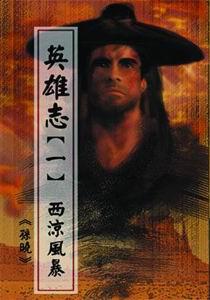世间最可恨的死敌,并非官场政敌,亦非沙场宿敌,而是「情敌」。不想可知,苏颖超心中最恨的情敌,正是那素昧平生的「卢云」。这滋味卢云也尝过,那时他听说顾倩兮嫁与旁人,锥心刺骨,险些泪洒当场,此人生第一大苦也。无奈未婚妻谁不好嫁,竟嫁了杨肃观,成了昔年旧识的枕边人,此人生第二大苦也。簧夜思之,辗转反侧,只想找人一吐衷肠,偏偏自己亲逝友散,举目无亲,又没了功名官职,惶惶如丧家之犬,这三苦齐涌心头,逼得他痛苦彷徨,连北京也不愿回来。爱憎怨、离别苦,自己已然伤心欲绝了,可苏颖超的处境更糟,自己好歹还认得杨肃观,深知此人貌如曹子健、志如曹阿瞒,手创「镇国铁卫」,本乃当代一大枭雄,绝非床第亵玩一类小人。顾倩兮嫁了他,至少不算辱没了。相形之下,苏颖超却不认识自己,眼皮一闭,杂念丛生,不知多少不堪入目之事飞入心田,全贴到了琼芳身上。卢云一生问心无愧,虽王天下而不存与,可若真坏了琼芳的名节、逼死了苏颖超,这辈子全算白活了,今日此时,便拼着性命不在,他也要把事情问个明白。大雪扑面而来,卢云却是越奔越快,沿着茶堂后的小径奔出,只见雪地里有着足迹,正是琼芳踩出来的,卢云急起直追,奔过了小径,面前却多了一道矮墙,一个纵跃,便已翻了过去,霎时之间,竹林碧涛,迎面而来,登让他「啊」了一声,忍不住怔怔停下脚来。时令彷佛到了夏至,来到了江南,放眼望去,漫山遍野全是绿竹,正是红螺三景之一的「御竹林」。相传这片竹林是蒙古人自南方移栽而来,由鞑虏胡皇亲手栽下,没想却意外在北国寒地里活下,从此成为红螺奇景之一。满天霜雪,可乍见了这片竹林,却彷佛重温扬州时光,卢云边走边瞧,忽见林里有座房舍,门口却有一行足迹,忙奔了过去,却听屋里传来话声:「胡寺卿,你以为此事应该如何?」卢云微感失望,自知来错了地方,正要离开,又听道:「霸州新败,我『临徽德庆』责无旁贷,本王愿向皇上请罪!可今早二哥战死,却属祸起萧墙,非战之罪!胡寺卿!你是大理寺的头儿,本王今儿请你摘奸发伏,望你念在天下万民的份上,能出面主持公道!」卢云心下一醒,已知说话之人便是勤王军首脑之一、方才带兵入寺的德王爷。阜城门一场大战,上震朝廷,下慑万民,当时大敌当前,「庆王爷」却临阵退缩,抱头鼠窜,乱军闯向城门之时,竟害死了「勤王军大都督」徽王朱祁,如今当是在算总帐了。卢云本还急于离开,一听此间涉及天下大局,却反而掩身过去,来到墙下,俯身窃听。屋中脚步来回,计有二人徘徊走动,屋角处却还藏有呼吸声,一吐一纳,低缓有力,当是一位内家炼气士,想来功力不弱,卢云便加倍压低了呼吸,以免暴露身藏。脚步声来来回回,那「胡寺卿」却始终不发一语,听那德王爷催促道:「寺卿大人,如今火烧眉毛了,朝廷主战主和,两派吵得不可交开,你位居大理寺寺卿,却怎地一声不吭?你若担忧庆王日后挟怨报复?不妨坦率说出来!」听得德王爷百般催促,言下已有责怪之意,那「胡寺卿」终于开口了:「王爷何出此言?胡某若是怕事之人,当年如何敢得罪江充?家母又怎会为暴民所杀?这些往事,您也该知道的。」听得这席话,卢云心下恍然:「我道这寺卿是谁?原来是他,胡志孝。」景泰年间有位名士,曾与刘敬交好,屡番直言上疏,以致遭江充迁怒,家中横生大祸,这便是当时的「礼部尚书」胡志孝,此人还有个探花弟弟,便是与卢云同科的胡志廉,没想十年过去,当年的「胡尚书」已改坐刑席,成了堂堂的大理寺卿。胡志孝语气带了不满,那德王爷便又软下了口气:「寺卿大人,便算本王错怪你吧,可你自己怎不想想,你当年连江充也不放眼里了,现下不过参个庆王,却还顾忌什么?我看这样吧,这回弹劾上疏,我也不让你一个人担当,本王陪你一同署名便是了。」此番勤王军新败,本想这「临徽德庆」推诿卸责,定会把罪过一发推给「正统军」,以免朝廷追究,岂料这德王爷竟是秉公仗义,居然要上书朝廷,公开弹劾自己的亲兄弟了?卢云心里不由有些敬佩:「好个德王爷,这般大义灭亲,天下几人能够?」正肃然起敬间,却听胡志孝叹道:「王爷啊王爷,百姓常说:『打虎还须亲兄弟』,您此番拼了命的参劾自家人,究竟图的是大义灭亲?还是求得是壮士断腕?可真让老臣看不明白了。」德王爷大怒道:「你说什么?」砰地一声,一掌拍上了桌,震得茶碗喀喀作响,想是动上了怒。卢云听在耳里,却是恍然大悟,一时暗骂自己胡涂。天下没有不败的兵马,却有不倒的将军,这诀窍便在于「金蝉脱壳」四个字,看勤王军此番吃了败仗,庆王又害死了徽王。一旦朝廷震怒追究,「临徽德庆」人人有事,是以德王爷的当务之急,便是早日撇清关系,越早参劾庆王,越能显出自己的绝不护短,至于奏本上的署名,「德王」两字自是越大越好,最好能用手指血书,那才表得出「大义灭亲」四个字来。古人大义灭亲、今人断手求生,同是一刀斩下,用意却大不相同。德王爷听得讥讽,不免也恼羞成怒了:「胡大人!本王看你是个人物,与你谈理论事,如何出言嘲讽?也罢!就算本王走了眼,自己上奏便是!」胡志孝道:「王爷不必动怒,您怕庆王连累您,故而壮士断腕,以求自保,本也无可厚非。只是下官得问一句,这蝮螫手则斩手,蝮螫足则斩足,可若是咬上了头,莫非还真能切掉脑袋瓜么?」德王爷怒道:「你到底想说什么?」胡志孝道:「王爷,下官就明说吧,如今徽王已死、庆王在逃,倘使咱们真参劾了庆王,您想万岁爷接到了奏本,却要如何处置?」德王凛然道:「那还要说?皇上如此英明,一接弹本,即刻准奏,捉拿庆王到案。」胡志孝道:「所以您就不是万岁爷了。您且想想,勤王军是你们四个管着,如今死了一个,还要再抓一个,可转看阜城门外,却是灾民如海、蜂拥而来,闹得城里人心惶惶,都说京师守不住了。您若是皇上,真会选在此时查办庆王么?」这话提醒了德王爷,登使他咦了一声:「你……你的意思是……咱们不该在此时上奏?」胡志孝道:「正是此意。大战当即,咱们便算参了庆王,皇上也不会办人,反会责怪胡某不识大体、阵前换将、动摇军心。到时龙颜大怒,下官丢了这顶乌纱帽事小,要是也连累了载允的东宫大业,那才真是罪该万死了。」德王爷沈吟道:「这……这也太不合情理了,庆王触犯军法啊,皇上怎会如此护短?」卢云心中也想:「没错,庆王害死自家主帅,皇帝便再昏庸,也不该袒护他。这胡志孝不通军务,一至如斯。」正摇头间,却听胡志孝道:「王爷要谈军法,那老臣便教您一个官场上的兵法。您且想想,城外那帮怒匪,姓什么?」德王道:「都姓『秦』了。」胡志孝道:「那正统军呢?都姓什么?」德王道:「那还要说,一发都姓『伍』。」胡志孝道:「这就是了。怒匪姓『秦』,正统军姓『伍』,可城里城外、唯一姓『朱』的兵马,却是哪一只?」德王啊了一声:「是……是咱们勤王军。」胡志孝道:「是了,现今外有秦家贼,内有伍家军,朝廷上下风飘雨摇,最是该重用勤王军的时刻,皇上稳定军心尚且不及,您却急着望自家人身上参一本?这不是搬石头砸脚是什么?」德王啊呀一声大喊:「对啊!本王真是胡涂至极!怎没想到这一层来!」卢云心下一醒,总算也明白了胡志孝的思路,现今大敌当前,内外局势动荡,皇帝的当务之急,便是先抓牢一只自家兵马,是以他非但不会选在此时查办庆王,怕还要连升三等,大力重用,德王爷反着这条思路去走,自会坏事。德王爷低声道:「这么说来……我这份奏章……」胡志孝道:「不许上。就上了也没用,皇上只会把您召来责骂一顿,说您不晓事理。」这胡志孝无愧是两朝重臣,人情事理,把握得明明白白。这番话直把德王说得诺诺称是,卢云也是暗自叹息:「卢云啊卢云,枉你自称熟知兵法,这番剖析见识,你说得出口么?」卢云盖世文章,棋盘对弈,必在胡志孝之上,战阵对决,必也能稳操胜券,可到了官场,却定然一败涂地。其间道理,正是在于「人情」二字。在卢云眼里看来,勤王军、正统军,不过都是棋盘上的棋子,阵前杀敌,并无分别,却不知在皇帝的眼里看来,这些棋子其实大不相同,不仅分亲疏、别远近、尚且有自家军、外家军之隔,倘使卢云坐在胡志孝的位子上,只怕三两天便关到了牢里,连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了。屋里静了下来,那胡志孝入席坐下,德王爷则是叹了口气:「多亏寺卿大人提醒,本王险些误了大事。只是现今徽王已死,咱们究竟该怎么做,还得请胡大人提点了。」胡志孝道:「王爷既能体谅,那下官也就直言了。现今咱们的下一步,绝非是参劾庆王,而是先找到伍都督,先议定一个说法,到时朝廷上论起徽王之死,大家才不会牛唇不对马嘴。」卢云心下一凛,德王也是低呼一声:「大人是要伍定远替咱们遮掩?」胡志孝道:「没错。徽王死于阵前,可以是戮力杀敌而死,也可以是溃散败逃而亡,端看咱们的奏本怎么写。这一层必得伍都督从旁照拂。」德王低声道:「此事有些难处……这正统军向来和咱们不对盘,这伍定远又是个土人,怎会给咱们这个人情?」卢云心中也想:「没错,定远再傻,也不会陪着瞒天过海,为此欺上瞒下之举。」那胡志孝却有他的道理,听他道:「王爷,您别小看伍定远了,他能做到这么大的官,仗的是什么?正是因为『胡涂』二字。他懂得看大局、观风向,所以明白何时该睁眼、何时该闭眼。下官敢拍胸脯担保,伍定远见了咱们来,定会帮着遮掩,绝不会推辞。」德王爷喃喃地道:「那……那要是他不肯呢?」胡志孝道:「霸州一战,若非伍定远擅夺徽王帅权,勤王军未必便败,大家真把事情说开,谁都讨不了好。权衡轻重,我不信说不动他。」德王爷哑口无言了,卢云也是暗暗叹息,方知伍定远早已是朝廷大员,心思计较,自与当年的小捕头大不相同了。德王爷又道:「寺卿这话确有道理,不过今早城门大战,好多人都见了,万一马人杰发了狗疯,居然找了御史联名上奏,把实情全盘说出,那可如何是好?」胡志孝道:「这马人杰确比疯狗还凶些,不过老夫也不怕他。只要我和伍定远抢先一步把奏章送上,皇上心里有了底,这疯狗若还敢吠上一声,皇上定会打断他的狗腿。」卢云虽不知这「马人杰」是谁,但听胡志孝称之为「疯狗」,定是敢说话的一类,倒是可以认识认识。那德王爷又道:「大人,朝臣那儿都摆平了,可王爷们那儿呢?这关该怎么过?」事涉立储,屋子里便静了下来。卢云心道:「是了,朝廷里不只有定远,还有个八王。要想杜天下悠悠众口,只怕过不了这一关。」情势更错综复杂了,这八王不比朝臣,眼里只望着东宫大位,买不动、吓不倒,好容易勤王军霸州惨败、庆王又害死了徽王,天上赐下一个良机,岂能轻易放过?八王这关,最是难过,偏又非过不可。胡志孝心里有些烦了,只是反复踱步。德王爷道:「寺卿,小心驶得万年帆,我看咱们还是别冒险了,把庆王参了吧,便算万岁爷怪罪,总强过让人抓花了脸,万一戳穿这弥天大谎,到时皇上把手一缩,砍得还不是咱们的脑袋?」确实如此,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,皇帝虽想保庆王,却也不能不讲道理,庆王的丑事一旦揭穿,皇帝便想保他,那也保不住了,届时德王、胡志孝、伍定远这帮扯谎凿空的人,都得一齐倒。皇帝若是勉强来救,只怕连朝廷也要一起倒了。德王爷低声道:「大人,你怎么说?这庆王到底参不参?」胡志孝道:「不……参。」德王哦了一声:「怎么说?」胡志孝道:「杀头的买卖有人干,赔本的生意无人做。没错,庆王是一碰就倒,可别忘了,以现在的局势,谁想推倒他,谁便得和庆王一齐倒。」德王爷皱眉道:「你……你是说,不论谁来参庆王,便会落得两败俱伤?」胡志孝道:「没错,咱们几个是撒了谎,可这个谎却是皇上想听的谎!谁敢在这节骨眼上犯冲,谁就是和皇上过不去。到时辛苦推倒了咱们,自己却成了皇上的眼中钉,还不是白白便宜了别人?如此赔本生意,您想唐王、丰王算盘打得这般精,哪会干这傻事?」总说「鹬蚌相争、渔翁得利」,德王爷思索半晌,便也点了点头:「没错……出头木儿先朽烂,这可是同归于尽的架子,我看诸王这会儿相互牵制,那是谁也不敢动了。」胡志孝道:「我方才想过了,唐王、丰王都是深谋远虑的人,自不会在此妄动。其余诸王实力构不上,想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我所担忧的,只有鲁王与徐王。」德王爷嘿地一声:「没错,险些忘了他俩,这两个平日就分不清东西南北,要有人背后教唆,却让他们来做这个出头鸟,那可怎么办?」胡志孝道:「那咱们便得防在前头。王爷,您可认得他俩的身边人?咱们得想个法子打声招呼,疏通疏通。」德王爷沈吟道:「这鲁王那儿,我倒有个认识的人,便是王妃的父亲平湖君,这位崔老先生年轻时住在烟岛,受过我父王的恩惠。我一会儿可以过去说说,让他向鲁王妃递个话。」胡志孝道:「也好,这事就有劳王爷了。徐王那儿,王爷是否也有门路可走?」德王爷叹道:「大人,本王先明说了,徐王背后有个靠山,我说不动。」屋里再次静了下来,想来人人都与卢云一般,全都想到那响叮当的三个字:「杨肃观」。听得一声长叹,胡志孝好似累得瘫了,竟然没了声音。德王爷压低了嗓子:「寺卿,这杨肃观可不是什么善碴,要是他有意犯冲,那就什么都别谈啦。」胡志孝叹道:「我知道。所以我才没说话。」德王爷咳嗽道:「寺卿,昔日顾嗣源在世,你不是和他有些交情?你能不能去找杨夫人疏通疏通?」听得他们提到了心上人,卢云不由揪紧了心情,那胡志孝却叹了口气:「王爷这是异想天开了,杨家这个不比伍家那个好管事。您要我找顾倩兮说项,那是白搭了。」德王爷道:「什么杨家伍家,这话是谁说的?」胡志孝道:「这是宫里传出来的。」卢云闻言一愣,德王爷也是大感好奇:「怎么?这……这话是皇上说的?」胡志孝道:「没错,听说皇上前几日与丽妃闲聊,便说了这段话。他说不管事的女人就不弄权,不弄权的女人就不要钱。杨夫人不要钱、所以不弄权,说来是比他的干女儿高明些,便要丽妃多学着点儿。」德王爷忙道:「这个干女儿,你说得便是艳婷吧。」胡志孝道:「没错,就是伍夫人,皇上跟前的第一红人。」德王呸道:「什么第一红人?亏他伍定远练了一身神功,功夫都练到了脸皮上去吧?自家老婆不在家里伺候老公,反倒去宫里伺候了皇上?他不害臊,我还替他丢人哪!」这艳婷拜皇帝为父一事,卢云却也听人提过,好似当年伍定远成亲时,已然位高权重,艳婷却仍是民家村女,为使两家身分相偕,正统皇帝便收她当了义女,从此传为一段佳话,没想到了德王爷嘴里,却落得如此不堪。胡志孝咳嗽道:「帝王家收外姓为女,古来便有先例,汉唐天子更有收异族为子的,收个干女儿却算什么?何况伍夫人丽质天生,能言善道,皇上爱听她撒娇,那也是人之常情。」德王爷冷笑道:「是吗?那皇上又为何背后损她?」胡志孝咳道:「我话还没说完。那时皇上才把话说了,丽妃便接着应了,她说伍夫人要权、要钱、要面子,看似什么都要,其实没啥不好,一个人若懂得爱钱爱权,那便懂得爱皇上、爱丈夫、爱国家,可要是一个女人连钱也不要了,那她还要什么?早晚是个叛逆不孝的。」「他奶奶的!」德王骂了粗口:「这算什么鬼话?皇上听了以后,可掌了丽妃的嘴?」胡志孝道:「那倒没有。皇上说这话颇有道理,反面破题,值得深思。」卢云听得心惊肉跳,德王爷也是微微一凛:「这么说来,皇上还记着当年的事了?」胡志孝叹道:「可不是么?听宫里的人说,皇上每回只要一喝豆浆,便会想到顾嗣源的事,总得砸破十来个碗,连带把杨大人也骂上一顿。皇后娘娘只好吩咐了,要御膳房别再磨豆子,若把皇上气病了,谁来担待?」「两代朝议书林斋、专论天下不平事」,这些往事卢云自也听人提过,自知顾倩兮曾经开办书斋、忤逆天子、蔑视国家,依此看来,皇帝必也曾迁怒过杨肃观。卢云心下暗暗叹息,都说杨肃观冷面无情,「断六亲、绝七情」,可对待顾倩兮却很不同,若非有他,便十个顾倩兮也给杀了,如何还能活到今日?德王爷哼哼冷笑:「说到底,皇上还是疼他的干女儿多些啦,我怎说自己老斗不过正统军,他妈的伍定远,本王看他这一身军功,全是靠他老婆床上挣出来的吧?」卢云大吃一惊,胡志孝也是骇然不已:「王爷!你别信口雌黄!皇上没有子嗣,多疼干女儿一些,又有什么?你怎能如此口不择言?」德王爷呸道:「本王怎生口不择言了?皇上再怎么偏袒伍家,那也不能胳臂肘向外弯!真龙、真龙,就凭这两个字,便能杀他全家的头!」胡志孝忙道:「王爷听我一言,冤家宜解不宜结,你勤王军再怎么不济,也都是皇家血脉,指尖尖、心头肉,犯不着和外姓冲。为了载允着想,您还是多向伍夫人说些好的才是。」德王爷怒道:「什么?要本王巴结她、奉承她?他妈的一个烂婊子,本王要拍她马屁?那何不去向杨肃观磕头,也好求个二当家什么的?」这话一说,卢云心头大惊,胡志孝也深深吸了口气,道:「王爷言重了,杨党是杨党,伍家军是伍家军,这『威伍文杨』可不能混为一谈。」德王爷恼道:「为何不能?他俩不都是复辟里搞特功,大搞加官晋爵把戏的?」胡志孝道:「王爷,杨肃观是文臣,依着祖制,至今可还没封爵。」德王爷道:「本王看也快了!皇上不赏他,他便要自己赏自己啦!」听得此言,卢云心头更惊:「难道……难道杨肃观要谋反了?」这杨肃观位高权重,便与当年的江充相仿,可追根究底,他又与江充的地位大不相同。想人家江充是景泰的忠臣,宛如一体之两面,杨肃观却始终握着「镇国铁卫」不放,却要正统皇帝如何安心?想到那「修罗之令」便在自己身上,正胆颤心惊间,又听胡志孝劝阻道:「王爷,你怎说这话?这话连皇上也不敢说,你就这么出口了?你可知这牵连多大?整个朝廷即刻便能大乱哪!」德王大声道:「我怎么不能说?这杨肃观在朝里结党营私,那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么?胡大人!你敢说此人没有反心?」胡志孝恼道:「王爷,反贼这个位子,早已有人坐了,怕还轮不到杨肃观吧?」德王爷冷笑道:「轮不到他?等得文杨武秦里应外合,那才叫做美哪。」德王言语越发偏激,胡志孝也不禁动气了:「王爷,下官跟你挑明了说吧,当年没有杨肃观,便没有这个正统朝,你临徽德庆也没今日这般权势。饮水思源,咱们对待这批功臣,是否也该留点口德?」德王呸道:「好你个胡大人,一心一意都是替杨肃观讲话,你到底站在哪一边?莫非你也是个镇国铁卫?」胡志孝大怒道:「王爷要看我的手臂么?来!本官现下就脱袍子!」两人吵了起来,已是不可开交,忽听屋里衣衫微动,有人站了起来,道:「德王爷、胡大人,严某有几句话要说。」这嗓音清朗,说起话来中气笃厚,正是先前卢云察觉的那名内功高手,胡志孝收敛了怒气,喘气道:「严……严掌门若有高见,但说无妨。」卢云心念一动:「严掌门?莫非便是峨嵋严松?」先前卢云人在茶堂,便曾遇上一个叫做严豹的年轻人,自称是严松的晚辈,还说了好些立储的事,依此观之,峨嵋全派真已托庇到了「临徽德庆」门下。严松道:「王爷、大人,你俩在这儿高来高去,老道是一句也听不懂,也没心思来听。贫道现今只一件事请教,徽王爷无辜冤死,你们打算怎么向王妃交代?」胡志孝咳嗽几声,道:「严师傅,我实话实说吧,徽王的案子不能追,大战在即,你得放一放。」严松道:「怎么放?」胡志孝道:「死有重于泰山,亦有轻如鸿毛。咱们参了庆王一本,看似替徽王讨回了公道,其实只是便宜了其它几位王爷。现今局势,咱们只能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,把事情盖过去。」严松道:「所以照你的意思,徽王之死绝不能追究了?」胡志孝道:「没错,非但不能追究,咱们还得力保庆王。这才是上上之策。」屋里没了声息,只听得一声叹息,严松缓缓地道:「王爷、大人,实不相瞒,在下是载允的师父,肩上担着孤儿寡母,如今王爷尸骨未寒……」嗓音提起,厉声道:「你俩便想瞒天过海,纵放庆王这元凶大恶!我这儿请教一句,若是王妃娘娘责问起来,却要严某如何交代?」这话义正词严,直把卢云听得目瞠舌僵:「好个严松!十年不见,居然洗心革面了!」这严松昔日是江充的走狗爪牙,惟利是图,岂料十年过后,却能说出这番话来,当真是字字铿锵、句句在理。胡志孝却也恼了:「严师傅,王妃是妇道人家,看不懂事情的利害,岂难道你也不懂?临徽德庆,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,庆王一倒,『临徽德庆』便得一起倒!到时唐王、丰王发动百官上疏,说徽王爷治军无方、自乱阵脚,以致京师被围,那咱们还顶得住吗?那时载允陪着徽王爷一起入了土,王妃娘娘便开心了?」这话一说,严松便哑口无言了,德王爷也劝道:「严师傅,战场上的事情,向来是瞬息万变的。再说老四平日与二哥最好,若非情势所迫,哪会害死二哥?真要说元凶巨恶,自是秦仲海那厮,王妃那儿劳驾您去说说,二哥人都死了,咱们还能不为载允打算吗?」众口铄金,都要严松放过罪魁,不再追究徽王之死,可怜徽王这般地位,居然就要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卢云听得大摇其头,严松想来也甚苦恼,听他叹了口气,道:「这事我不能作主。师叔,您老人家怎么说?」听得「师叔」二字,卢云心下大惊,万没料到屋里还藏着第四个人?正骇然间,屋中木椅嘎地一声,真让人推了开来,听得幽幽叹息声响起:「离开京城几十年了……」话声稍停,轻轻又道:「还是什么都没变啊……」这嗓音带着七分感伤、却又藏了三分讥讽,屋里众人都静了下来,谁也不敢接口。过得良久,听得德王爷低声道:「白老爷子,您要觉得此事不妥,那便请说……您便要咱们上奏朝廷、弹劾庆王,那也没什么不可以……」胡志孝也改口道:「这个自然。徽王是您老人家的亲女婿,您老人家做主,咱们都听您的吩咐便是了。」[记住网址.三五中文网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