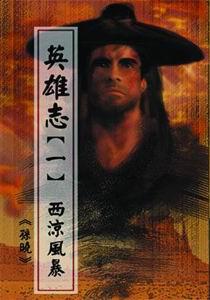空旷的院子里传来一声低咳,跟着响起一个北京来的嗓音,喝哩渣呼的。“赵爵爷,到底您家老六……”江充清了清嗓子,“成不成啊?”对面站着一个高壮胖子,年莫二十七八,他皱着眉,斜着眼,大脸模样开阔,但他方言浓重,一口呵嗨唔嘻的官话,嗓子全掐到一块儿去了。听他大声道:“江大人哪,赵醒狮虽远在天南,却也有些谋生法子,虽不比少林武当的威风,却也不容旁人小看。”江充听出他的不悦,立时笑道:“别动气,“抚远四大家,岭南赵醒狮”,江某身为太师,却也耳闻已久,谁又敢小看赵老弟?”他顿了顿,又道:“不过老弟啊,咱丑话得先搁在前头儿,您六弟这回要是失风被擒,坏了我的事儿,皇上那儿问起,我可不好交代了。”六代赵醒狮,双名称任勇,这赵任勇今年二十又七,五年前接任家长,这位少年英雄出身世家,脾气自比常人为大,听了奸臣质问,脸色登时沉下,神态竟是有些冷。赵家一向自高身分,便在权臣面前,神态也不见卑屈寸让。其实倒不是赵家人自命清高,实乃赵姓一族曾为皇族胄裔,若非蒙古铁骑南下烧杀,赵族也不会南迁湖广,成了今日的岭南赵家。便连领受朝廷爵位都让这家人感到屈就,却要赵家子孙如何把江充放在眼下?耳听江充不断怀疑挑衅,赵任勇再也沉不住气,只见他壮大的身子缓缓站起,道:“江大人,跟您说件往事吧。”他见江充嘴角含笑,模样不屑,登时手指门上对联,大声道:“这联子有个来历,您要是听了,便能信我赵家的能耐!”“哦?”江充故意眨了眨眼,脸上泛起了微笑。中原之大,无奇不有,便随意挑一座庄,从里头扔出一块砖,往往也有三五百年历史。这赵家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,自也有说不完的故事,看赵任勇这般神气,这门联八成有什么奇妙之处。江充本意只在激将,听他中计,便自嘿嘿一笑,抬头去看那对联。那对联左右各一,门楣上另加四字横批,初看乍见倒也没甚稀奇,江充打了个饱嗝,高声念道:“古往今来,盘龙舞狮称第一。”当年赵家南迁湖广,皇族身份不再,几百口人坐吃山空,再多家产也不够使,天幸赵家有个武功高手,他把太祖拳法融入舞狮阵,创了醒狮团出来,这便是第一代的“赵醒狮”。赵家无所不练,梅花阵、力马阵、八卦阵、蜈蚣阵,无一不精,也难怪要自夸“盘龙舞狮称第一”。这话虽不免有些狂气,但赵家族人舞狮确实精到,也不能算他们吹牛太过。这上联不见奇怪之处,江充又打了一声饱嗝,探头再看下一联,忽然间咦了一声,念出了荒唐的下一句:“天上地下,装神弄鬼我最行。”读到这里,任谁都会相顾骇然,江充再去看横批,更是忍俊不禁,霎时捧腹大笑。“万莫回头”,这便是赵家的横批。这幅对联既粗且怪,读过的人自是诧异不解,不知这是什么浑人写的,江充大笑道:“万莫回头?你家也养了怪物么?”当年神机洞里有只“长右”,一见生人回头,立时扑上便咬,想不到岭南赵家也有这等悬疑,却让江充忍俊不禁了。“江大人别取笑在下。这是我五年前接位时写就,为了这幅对联,我还立个门规下来。”江充看了横批一眼,笑道:“什么门规?万莫回头么?”赵任勇啐了一口,道:“江大人别闹了,不能转头还了得?那不连马都不能骑了?咱的门规是:“严禁背后吓人”!”江充听了这话,只感莞薾不已,以为他有意说笑。赵任勇却没多说什么,是不是说笑,唯独赵家的老奶奶知道了。※※※事情要从十年前那个既闷且热的下午说起……那年赵任勇不过十七岁……炎夏午后,热得紧,恰是午睡的好时光,嗡嗡蝉鸣中,只见一名老奶奶躺上后院凉床,正自呼呼大睡。看这老太婆睡得口水横流,一旁又有大批婢女煽风纳凉,能有这般好清福享用,这老婆婆自是赵家的老太君无疑。凡人年纪越大,脾气越拗,自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怪僻生出。这老婆婆年过古稀,七十又三,更是怪中之怪,癖中有癖,不管吃喝拉睡,习性都与常人大大不同,其中后院午睡这一条,更是老太婆的最大癖好,不论刮风下雨、天暖天寒,她老太婆日无间断,一过午时便去躺下。赵府上下都知老太太火气大,便严禁调皮的孙儿在院中吵嚷。赵家有七个孩子,老大便是后来名震华南的赵任勇,老二则是日后狮团的武功教头赵任通,赵家的孩子们打小就有出息,当然也不会有人忤逆家规,过去找老太太晦气。天知道,事情便是从午睡里闹出来的……那年太后老佛爷做寿,醒狮团方从北京归来,带回宫中不少赏赐。其中更有只来头不小的毽子,那毽子白金所就,雕做孔雀形状,雀眼镶着两只红宝,雀尾更是真正的孔雀花翎。光看便知价值不菲,七个孩子见了,自是大声嚷嚷,无不要父亲赏给自己。“五代醒狮”赵全笑了笑,随口交代围拢过来的子女:“别吵、别吵,咱家有七个孩子,毽子却只有一只。爹爹不管赏给了谁,都是偏心。”他摸了摸孩子们的小脑袋,笑道:“这样吧,你们比一比,谁要踢得好,爹爹就赏谁。”说着把毽子往天一扔,便自转身离开了。七个孩子欢声大叫,便在天井里踢起毽子。赵家醒狮为生,家中不分男女老幼,自小便练武强身,毽子有助腿力身法,尊长早已教导他们玩耍。此时有了赌注,孩子们更是加倍卖力。孩童们来回玩耍,你一记我一记,大的踢给小的,依次以下,事先还言明了,谁让毽子落地,谁便随二娘到后厨帮伙,这活儿光听便累人,孩子们自是使尽了全力。咻地一声,毽子往老六那儿飞去,五妞儿是个十岁女孩,向来喜欢欺侮六弟,这一踢既斜且歪,登让老六赵任宗慌了手脚。情急之下,拿着脑袋奋力顶去,毽子飞上半空,直直落到后院去了。“哦……你完了……”其它几个孩子同围上来,对着赵任宗指指点点。赵任宗涨红了脸:“什么完了?我接了五妞的招,下个该是老七接,哪里输了!”老七是家中幺儿,一向备受父母宠爱,他听了这话,登时扁嘴要哭,五妞儿与他是一母所生,自然要出头维护,只听她嘻嘻一笑,道:“老六你可傻了,大家是说你完了,又不是你输了。你耳背啊,怎么连话也听不清楚?”赵任宗年纪虽小,脾气却不小,他一把往五妞儿身上推去,喝道:“你胡说什么,贱婆娘!”老三冲了过来,喝道:“你干什么?动手打人么?”大户人家姬妾极多,赵全有三个老婆,共生了七名子女,几个孩子年纪虽小,但眼看生母彼此钩心斗角,长年耳濡目染之下,早已按着母亲的心情分帮结派,这老三与老幺一个长相,自也是三娘所生。此时见六弟发威,自来帮弟妹们出头。赵任勇身居长子,比六个弟妹大了七八岁,眼看弟妹们打成一团,自要出面调解。他咳了一声,道:“别吵了,老六,毽子是你踢到后院去的,你去捡回来。”连素来公正的大哥都这么说了,赵任宗自是吓得全身发软。捡毽子简单,但后院那个鬼婆可不简单了。想到后院的暴躁老太婆,赵任宗面色发青,只想出言拒绝,一旁五妞儿语气不善,冷笑道:“把太后赐下的宝贝搞丢了,一会儿爹爹问起,你还想活命么?快去捡吧!”赵任宗苦着一张脸,想起这毽子非同小可,别说值得几百两银子,还是太后赏下的宝贝,实在丢不得,当下只得哀叹两声,点了点头。※※※一柱香时分过去了,赵任宗心惊胆战地蹲在后院,偷眼打量院中情势。大大的榕树遮住烈日,树荫下躺着一个老太婆,正在凉床上呼呼大睡,两旁婢女手举蒲扇,徐徐煽凉,模样很是清闲。日光照耀,凉床下射出两道红色光芒,正是白金毽子的孔雀眼在发光。赵任宗又喜又怕,白金毽子就在眼前,只要自己能爬到床边,东西自也能到手了。只是天下事知易行难,便连捡个毽子也是一般。老奶奶脾气大,火气足,生平只爱外甥女三娘,对大娘、二娘恨之入骨,见面便骂,对她们的子女自也透着不善。只是大娘出身淮西天将府,有大哥高天威背后撑腰,又生了老大赵任勇,双重屏障之下,那是谁也不怕的局面,说来说去,便只可怜二娘一个人了。那赵任宗是二娘的独子,平日自被家人排挤欺侮惯了,往常只要见了老太婆,立时脚底抹油,速速开溜,哪料到今日却要落入她的魔掌之中。赵任宗深深吸了口气,看老奶奶这懒模样,八成已经睡熟了。他趴在地下,拿了只荷叶盖在头上,把自己当作一朵大荷花,跟着缓缓爬向凉床,朝那只白金毽子蠕动而去。夏日炎炎,婢子们眼神松散,煽凉时有气无力,不曾发现荷叶竟在自行爬动,赵任宗心知肚明,他最要担忧的唯有老奶奶一人。老太婆武功高强,目光锐利,要给老虔婆撞见自己,届时只要往自己头上安个吵嚷午睡的罪名,他老六没准玩完了。赵任宗心念于此,登时憋住了气,加倍小心爬动。五尺、四尺、三尺,自己已在凉床旁二尺远近,白金毽子触手可及,赵任宗正想伸出手去,忽然老太婆身子翻转,脸面转动,却是朝他这面看来。赵任宗大吃一惊,吓得全身发抖,当场把荷叶盖在脸上,管他是死是活,心惊之下,先来个掩耳盗铃再说。过了良久,倒没听到老太婆的怒吼声,赵任宗大着胆子,把荷叶推开,凑眼去望,只见老太婆睡得横七扭八,梦中睡姿丑恶,两腿敞开立起,着实难看至极。赵任宗小嘴一歪,想起娘亲平日专给这老太婆欺侮,登时低声作呕。眼看老奶奶不曾发觉自己,他便定下神来,再次伸出手去,朝凉床底下的白金毽子摸去。只等找回毽子,他便要溜之大吉,一会儿自能过去耀武扬威了。摸了良久,迟迟没有东西入手。赵任宗皱起小小眉头,又往床下乱摸一阵,只是捞来掏去,还是只有黄软软的泥土。赵任宗心慌起来,赶忙趴到地下,凑眼去望,这一看之下,身子却凉了半截。床下空荡荡一片,别说毽子,连只虫子也没有。怎么搅得?白金毽子不见了?方才还看到的东西,哪知竟会杳然无踪?想起这东西是爹爹带回来的宝贝,要是在自己手上弄丢,不知会有什么大祸。赵任宗泪眼汪汪,拼命在地下搜寻。“你在干什么?”凶狠的声音赫然响起,赵任宗知道玩完了,他红着眼眶,抬头望着祖母,小声回话:“我在找毽子。”“找毽子?找毽子找到我这儿来了?该死的浑孩子,不晓得你娘怎么教的?”伴随着老太婆的指责,他的耳朵已给拎了起来,赵任宗惨叫道:“不要这样…我只是在找毽子啊,只是找毽子…找毽子…毽子…呜呜…呜呜……”他断断续续,已然疼哭了。毽子啊……你在哪里啊!※※※白金毽子就这样不见了,赵任宗也给打得死去活来,爹爹骂他粗心大意,奶奶说他不守家规,几个兄弟姊妹更说他是贼,竟把白金毽子独吞了。爱子既是小贼,从此二娘地位更低,赵任宗更加孤僻,再也不和兄弟姊妹玩了。三年后,母亲积劳成疾,终于病死,临终前赵任宗独守病榻,低声问她:“娘,你也当我是贼么?”二娘微微一笑,抚摸着爱子的脸颊,说出了最后遗言。“傻孩子,毽子是奶奶拿走的,你还想不通么?”赵任宗放声大哭,在那一刻,他忽然长大了。泪如雨下中,他心里暗暗立誓,他要把毽子讨回来,他要告诉家里每个人,他不是贼,奶奶才是贼。从此赵任宗像是疯了,他每天挂着重重一串铃铛,在家中四处徘徊,叮叮当当的声响中,铃铛老六的外号不胫而走……※※※“怎么讨?”两年后,从北方回来的大哥过来看他,这样问着六弟。“当然是光明正大的讨回来。”景泰二十八年,已经十五岁的赵任宗沉着嗓子,回答着正直的大哥。长兄如父,赵任勇是家里唯一还关心他的人。赵任勇叹气摇头:“别傻了。老太婆凶得很,你娘便是给她活活整死的,你可别自找麻烦。”赵任宗的嗓音更沉,“大哥放心,我轻功天下第一。靠着绝活,我定能把毽子讨回来。”赵任勇愣住了,登时嘿了一声:“这话家里说说可以,莫到外头丢份去!你可听过九华山?人家青衣掌门才是轻功第一!老六你年纪轻轻,不知天高地厚,说话可别太狂了。”赵任宗冷冷一笑,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,谁高谁低空口无凭,总要比上一比,不是么?他淡淡地道:“大哥,要比飞得高、纵得远,我当然比不过青衣秀士。”赵任勇哦了一声,问道:“莫非你跑得比他快?”赵任宗摇头:“论快,我也比不过江东解滔。”赵任勇忍不住咳嗽一声:“那你还敢说什么轻功第一?”赵任宗微微一笑,继续说道:“大哥哪……轻功之所以叫做轻功,正是因为那个“轻”字啊……”他眼中燃起了火焰,凝视着大哥的双眸。赵任勇这两年不在家里,自不知六弟挂着铃铛四处跑的事情,眼看六弟神色执着,倒也不便泼他冷水,只拍了拍他的肩头,以示安慰。赵任宗知道他不相信自己,却也没说什么,只是笑了笑,但他的眼神执着依然,带着完完满满的自信。※※※“毽子还我。”那天风和日丽,正吃着早饭的老奶奶神清气爽,老迈年高的她一向耳背,哪知先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么一句怪话,跟着左肩更被人拍了一记。她咦了一声,急忙回过身去,只见远处婢女在那哼歌摇摆,背后别无他人。老奶奶怒道:“大胆!谁让你碰我的!”那名婢女当场被打折了一条膀子,再也不敢靠近老太太。正午时分,老奶奶上茅房解手,这会儿轮到她嘴里哼着小曲儿了,忽然之间,又听到那句一模一样的话:“毽子还我。”老奶奶大吃一惊,陡然间右肩又被人重重打了一记,慌忙回头之下,除了茅房门板,依旧空山寂寂。老奶奶脾气不好,咒骂几声之后,决定找个道士过来驱鬼。下午时分,老奶奶纵然心情烦躁,凉床上的那场午觉还是要睡的,有了先前鬼惊妖声的例子,她找来十名婢女,前后左右围在床边,层层守护之下,自己终能放心呼呼大睡。睡熟了,身子翻过,脸面朝下,霎时又听到那句话:“毽子还我。”伴随这句怪话,她的脑门又给拍了一记。老太婆大怒欲狂,霎时睁开双眼,眼前没人,她坐起身子,回转头去,这回却见到了鬼。一张挂在榕树枝上的鬼面具。万莫回头啊,老奶奶真给吓死了。遗物中果然给人搜到了一只毽子。却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,据婢子们说道,那日午后她忽然正坐起来,之后便自行倒了下去,再也没动上一下半下。事后赵任勇找了六弟来问,老六便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说了出来。还加了这么几句话。“大哥,若说盘龙舞狮,当世你第一,要论装神弄鬼,天地我最行。”看着六弟身上挂满铃铛,在校场里奔来跑去,那铃铛却没发出半点声响,赵任勇自是骇然无语。既能轻,便能巧,然后动静自若,行止如魅,数年来赵任宗苦练不坠,加上天赋异禀,终于无师自通,练就了这身说嘴的本钱……赵任勇没有惩罚六弟,也未将事情泄漏出去。六弟不是老太婆的眼中钉,真要说谁是老太婆最痛恨的人,那就是大娘生的自己。少了老太婆撑腰,平日嚣张的三弟再也无法造次。待赵任勇接下“六代赵醒狮”的大位,登即写下这幅怪异对联,还立了一道奇怪门规,严禁背后吓人。江充听完故事,登时哈哈大笑,道:“赵爵爷果然精明,你六弟哪天要是觊觎庄主大位,往你肩上就这么一拍,那可不是好玩的。”江充老谋深算,才把故事听过,便知赵任勇这幅对联是写给六弟看的。一来表明对他一身轻功的敬意,二来也提醒六弟别来对付自己。江充日理万机,宫廷争斗在他都算家常便饭,何况这些闲事?三言两语间,便已看破赵任勇的用心。赵任勇咳了两声,道:“江大人取笑了。只是您说说,凭着我六弟的身法,天下还有他进不去的地方么?”江充看着门上的对联,点了点头。霎时间,嘴边现出一丝冷笑。当年刘敬这般厉害手段,还不毁在江某手里?区区一个天绝和尚,却凭什么心机城府,居然想与我江充斗?嘿嘿,任那“潜龙”潜得再深,王座之下能人万千,终能揪出海底下的神龙尾……※※※羊群中走出一名男子,身上挂满铃铛,看那人左侧距母羊半寸,右侧邻小羊毫毛不到,但一路行去,羊儿却分毫未惊,只任凭那人缓足移步。炎夏燥热,树荫下却甚凉爽。此处距达摩院已在百尺,自须万般小心。那人停下脚来,彷如一棵无声古树。他四下打量几眼,确信四周无人,便朝达摩院行去。这人身法不见得快,却非常柔静,也只有这般身手,江充才会惊为天人。大汉将军,御前四品云都尉,这便是赵任宗从江充手中得来的富贵。昔日不管是刘敬还是柳昂天,对赵家这个六弟都曾耳闻,也都曾差人过来,询问赵任宗是否有意任官,只是赵醒狮一家不愿扯入朝廷三派恶斗,自不愿六弟到京城办事。但天不从人愿,年前刘敬垮台,怒苍再起,江充独大的时刻已然到来,赵醒狮不敢忤逆权臣,也只有荐保六弟为官了。达摩院,实乃武林传说的圣地,若非赵任宗这般身手,谁敢贸然去闯?赵任宗望着眼前的达摩院,心里反复思量江充交代的几句话。据这位权臣言道,达摩院里关了一个要紧人物,便是曾让天下群豪闻风丧胆的魔头,人称“潜龙”的大军师朱阳。今番天绝出手,怒苍群豪之所以心甘情愿来到少林,便是为了此人而来。只是江充心中猜疑,这天绝僧闭关多年,少与朝中大臣往来,今番忽尔多事,莫非其中另有隐情?也是为了解开疑窦,便要自己出马打探,把个中内情查明了。一来察看“朱阳”是否真在达摩院,二来弄清楚天绝的用意,以免情势有变,反而给人将上一军。既要打探声息,便要深入龙潭虎穴,只是少林寺不比别的地方,甭说四大金刚武功高强、天绝师徒智勇兼备,便是“潜龙”自己,怕也是罕见了得的可怖人物。看这达摩院阴森至此,谁敢贸然去闯?赵任宗微微一笑,狼吃肉,狗吃屎,鸡鸣狗盗之徒虽然模样难看,却也有生存之道。他赵任宗虽只二十一二,但面对那帮吃肉虎狼之时,他可一点也不怕。赵任宗提起真气,脚踏干枝枯叶,肩膀四肢不用力,提气轻身,从枯叶上直滑过去,这一路滑来轻飘飘地,竟未发出半点声息。解滔当年与杨肃观激战一场,曾以“足立针”的绝技傲视群伦,此时若要见了赵任宗这手寂静无声的轻功,怕也要自叹不如。※※※无声无息地浮上墙头,静悄悄的黑影飘入院中。赵任宗打量着四周,达摩院古旧窄小,梁宇樯檐颇有残破。这等老旧房舍最难侵入,非只因建物腐朽,实因四下老鼠众多,这些鼠辈机敏过人,只要稍稍不慎,便会受惊四窜,届时吱吱声响发出,定会给人知觉。也是为此,赵任宗便带来细小铃铛,这种铃铛以声音低微著称,纵使猛烈摇晃,身边之人也闻之不清,赵任宗便以此留神自己的脚步,以免生出意外。穿院进门,缓步入堂,赵任宗隐身门板之后,屏住了呼吸。天绝僧号称寺中第一高手,耳音必定灵敏异常,自己的呼吸若要稍稍沉重,便会给人察觉,此刻已入虎口,定须万般谨慎小心。赵任宗静下心来,听见了院中风动林稍、蝉鸣鸟叫之声,他再侧耳倾听,察觉了墙下鼠洞中的老鼠鸣叫,那啾啾鸣响虽甚低微,在他听来却似震耳欲聋。再静下心来,方圆百尺内没有那股冷冷的寒意。天绝僧不在堂内。耳朵不如心灵管用,赵任宗自幼在长辈打骂下过活,早练就一套察言观色的妙法。旁人还没发怒斥骂,他身上的寒毛便会自行竖起,寻常人的心境尚能知觉,那帮武林高手的杀气浓如鲍鱼之肆,百尺外便能让他寒毛竖立,更是易于趋避许多。大剌剌地走入堂中,赵任宗四下探看,只见达摩院内梁高庭深,墙上挂满朝廷黄榜,太祖、太后、皇上,历代的封赏馈赠不计其数,此处果然是朝廷倚仗的圣地。依着江大人五千两白银买回的消息,堂上似乎有只木鱼机关,只要拉动了,便能开启密道。赵任宗左右探看半晌,便已发觉了佛桌上的木鱼,他再次聆听四周,确信院内无人窥伺,登即拉起木鱼,发动了机关,让堂内的暗门升起。墙壁下果然现出了一条密道,望之幽暗深邃。赵任宗嘴角泛起了微笑,少林寺的密道名闻遐迩,哪知即将被外人闯入,看来满山和尚都要灰头土脸了。※※※赵任宗缓缓跨步,行入甬道之中,他没有蹦跳纵跃,只老老实实的拾级而下。行不数步,果见黑暗中几只老鼠伏伺梯旁,彷如守卫一般。方才自己若要卖弄轻功,纵跃不休,此刻定会惊动鼠群。好热……这甬道青石所就,既陡且长,里头更是气闷。赵任宗行过百丈,忽然一阵凉风吹来,气息忽尔通畅许多。他往前再走几步,眼前赫然开朗。只见前方一处天然石穴,空旷宽敞,仰头看去,上头日光隐隐,这穴顶竟有数十丈之高,看日光从缝隙晒入,这石穴必然直通山顶。赵任宗不知这石穴作何之用,当即伸手抚摸四周石壁,入手处颇见湿滑,却没摸到青苔。他心下一凛,知道这地方经过一番清理,想来是为了对付怒苍群匪,只不知个中奥妙何在了。赵任宗自知猜想不透,摇了摇头,便顺着甬道往下走去。少了日光映照,眼前倍加昏暗,越走越难辨认道路,他从腰囊取出璘粉,朝半空挥撒过去,磷光照耀之下,前方现出了两条去路。赵任宗有些纳闷了,若照江充大人的交代,这地方本是座地牢,专来看守怒苍山的潜龙军师,照理来说,信道越少,越易于看守,怎需挖出两条信道来?嘿嘿,有点意思了,赵任宗眼中闪烁精光。他抚摸岩壁,虽然看不清晰,但入手摸来,一处满布青苔泥灰,一处却甚平滑,想来也是新近挖掘而成,时辰有限,不能一条一条地探查,只能任选其一察看了。他望着眼前两条信道,心中暗暗盘算。自己排行老六,那是偶数,偶为右,奇为左,那便往右边走吧。既然下了赌注,倒也不必再多想什么,自管放步潜行。江湖中人出外行走,生死间多少看点运气,他自信老天爷定会眷顾自己,心中倒甚宁定,丝毫不感惊惶。走过百尺,甬道间越来越昏暗,地势也笔直往下,忽然间,眼前闪动着火光,赵任宗心下一凛,知道前头有人,登时放缓了脚步,不敢稍动。哒、哒、哒,背后脚步声响起,赵任宗听了一阵,已知来人身体轻盈,这步伐如此密集细碎,自不是传闻中高瘦过人的天绝僧。赵任宗秉住呼吸,后背贴墙,把身子隐在黑暗之中,来人不管是谁,达摩院中都没有好惹的人物,自己若要给人察觉踪迹,必是死无葬身之地。脚步声越来越响,忽然鼻端闻到一股幽香,赵任宗心下一凛:“怎么搞得?这和尚擦得这般香?”他心下正自起疑,忽见一名女子从面前穿过,手上还拿着一只竹篮,看这女子面容艳丽,年约四十好几,却是一名标致动人的中年美女。赵任宗大吃一惊,不知少林寺严禁女子入寺,这里怎会藏有女子?而且藏的还是个大美人?实在不能不叫他满心诧异。赵任宗正自疑惑,那美女却没察觉自己,只往甬道下头去了。赵任宗放缓脚步,便从背后一路追踪行走。走不数丈,那女子伸手推开一道石门,轻声道:“皇上,咱们吃饭了。”皇上?赵任宗听那门里非但有人,甚且还让那女子唤做皇上,忍不住大为诧异,吃惊之下,身上铃铛便响了起来。赵任宗面色铁青,全身冷汗涔流,当下急忙定下心神,就怕给人知觉了。天幸那铃铛只响了一两记,声音也甚低微,自不曾惊动门里的人。只听石门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,叹道:“唉……还要在这儿待多久?实在想出去晒晒日头。”那人说话声音有气无力,浑似个重病之人,赵任宗心下暗暗奇怪,想到那女子方才的那声叫唤,忖道:“这人到底是谁?怎会给人唤做皇上?难道也跟咱太爷一个疯样么?”他赵家是皇族后裔,小时太爷疯疯癫癫,喜欢自充皇帝,还自号“宋德宗”,便要他们这帮小辈唤他皇上,后来五岁时家里受了朝廷爵位,这才停口没叫。照此看来,门里男子八成也是个失心胡涂的。正想间,那女子道:“皇上喝点汤吧,您这些日子胃口不好,可别搞坏了身子。”猛听当啷一声响,好似打破了什么碗盘,那男子大声道:“不吃!不吃!好容易从神机洞出来,却又跑到了达摩院,一样的不见天日!天绝大师人呢?叫他过来!”那女子慌道:“皇上息怒。怒苍山的人马不日便要上山,大师这会儿在安排双方会面,想来事情只要一妥当,您便能离开了。”那女子跨门入内,声音越来越低,依稀听那男子道:“躲躲藏藏几十年,朕实在心灰意冷。武德侯死了,刘总管也成不了气候,这回天绝大师若再失手,朕实在撑不下去……”那女子低声道:“皇上放心,这回天绝大师找了您的堂弟做帮手,那是万事不愁了。听大师说,他这几年改名换姓,在朝廷埋伏已久,谁都不知他的真正身分,说来比刘敬的城府更加厉害,定能对付江充……”那男子哦了一声,低低问了几句话,接下来那女子将石门关上,便已一字不闻了。赵任宗反来覆去地想着那几句对话,“躲躲藏藏几十年,﹃朕﹄实在心灰意冷……”想到那个“朕”字,赵任宗登感全身大震,心下着实骇然。小时候太爷喜欢关起门来做皇帝,却也不敢言必称“朕”,否则日常出门见客,万一说溜了嘴,那还不落个杀头下稍?只是门里那人并无分毫做作,随口说话间屡次称“朕”,显得十分自然,这口头禅若没用上几十年,要他如何能够?赵任宗惊疑不定,这里既是达摩院,当只有少林和尚住居,按江大人的说法,最多再关一个潜龙军师,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美貌女子,尔后又有人自称是朕?赵任宗有意查个水落石出,便行到石门之旁,贴耳倾听,只是他内力有限,却不能听闻门里细微声响,想要推开石门,却又怕惊动天绝大师,思来想去,还是只有火速离开少林一途,想来只要能面谒江大人,把此间情事全盘托出,料来以当代权臣的心机,定能猜知其中奥秘。赵任宗心念甫定,立时便往后头转身,赫然间,鼻中一痒,甬道中飘入了一股香味,他嗅了嗅,却是一股淡淡檀香,乃是出家人身上独有的味道。赵任宗慌了起来,知道天绝僧已在左近,方才那记铃铛声虽低,却瞒不过绝世高手的耳去,想来是把他引来了。他心中忐忑不定,知道立时便得离去。他不敢沿原路退回,眼看甬道笔直望下,地底应当另有出路,赵任宗加紧脚步,便往下一路奔去,他身法虽疾,身上铃铛却分毫未响,足见身法之轻盈,几与虫蝇相似。又奔片刻,眼前已有点点光亮,看那光芒明亮刺眼,正是炎炎盛暑的炙人烈阳,赵任宗大喜,知道出口仅在丈许之外。赵任宗脚步加快,正要奔出,忽觉背后一阵寒意发作,这杀气好生逼人,直从甬道迫来,忍不住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心惊之余,自知背后高手已在十丈不远,他憋足了气,把身子向前狠狠纵出,霎时双手触上冰冷石墙,举掌力推,嘎然声响中,石门已然打开。赵任宗松了口气,自知救回了性命。只要离开达摩院,仗着自己的无声轻功,山林泉水皆可藏身,在那大千世界里,谁还抓得到一只小跳蚤?他嘘了口长气,斜身闪身,跨出了石门。烈日逼人,耀眼阳光照上脸庞,赵任宗眼前一花,什么也看不见了,他把双目闭紧,身子背转,急急掩上了石门。当下略略放松心情,缓缓转过身去,便要离开。却在此时,身子碰上温温热热的东西。老天爷!背后站了一个人!“你……是……谁?”赵任宗的声音带着惊恐绝望,以他的心思机敏,居然没查出背后有人埋伏?他想把对方的脸面看清楚,偏偏日光刺目,自己方从黑暗出来,目不能视,当下茫然张眼,两手乱挥乱抓,好似盲了一般。耳边传来一声苍老低笑,跟着一只手摸上了喉咙,笑道:“你又是谁?”自弱冠之年练成轻功,赵任宗向来迂回御敌,从不曾真刀真枪的与人正面硬干,更不曾被人拿住要害,那人手指一摸上喉头,赵任宗惊怕之间,双足一点,立时朝背后纵去,要离开那人的掌握再说。碰地一声轻响,背心不及碰上石门,便感一股剧痛传来,那疼痛直传后心,逼得他几欲惨叫。这门是他亲手掩上的,可直到此刻,赵任宗方知门后安了一柄利刃,直戳后心要害。玩完了。方才目中刺痛,没曾留意门上有无机关,谁知背后竟多了柄杀人利器。鲜血从背后滴落,利刃随时透心穿过,在这生死绝命的时刻,一生勤修苦练的轻功终于派上用场。赵任宗的身子赫然凝住,他双足灌力,仗着身子灵巧过人,硬生生凝住了后仰之势。看他脚尖翘起,身子后仰,双臂撑开,全以脚跟力量支撑身子,只要重心往后一倒,利刃穿透身体,必然当场惨死无疑。前额冰凉,一根手指推来,抵住了自己的额头,只听那人笑了笑,问道:“想活命么?”这根指头只要稍稍用力,自己重心不稳,便会往后倒下,当场便活活戳死,赵任宗泪水洒落,慌忙间只在点头不止。那声音淡淡地道:“谁派你来的?”赵任宗世家出身,无须替江充出死力,哽咽便道:“是江大人。”那声音哦了一声,道:“他派你来作什么?”赵任宗又怕又惊,忍泪道:“他……他派我来找“潜龙”……”那声音哈哈笑道:“原来如此啊,您可辛苦了,快回去交差吧。”那手指微微用力,向前压落,虽仅蝇虫微力,但赵任宗身形本就不稳,全仗着轻功心法维持不倒,手指赫然推出,力道虽轻,却已让赵任宗往后摔下,他尖叫起来,扑地一响,后背撞上石门,霎时身子一寒,利刃已然透体没入。※※※“救命啊!”赵任宗大哭大叫,他没有死,他只是奋力向前一扑,连滚带爬地逃走。赵任宗发狂大叫,疼痛惧怕间,自然不敢回头去望。只见背后石门血迹斑斑,哪有什么匕首利刃,却只突了根一寸不到的卯钉。看那卯钉两面成尖,一面钉入石门,一面朝外突出,尖锐处不足一寸,纵使全数没入体内,也要不了性命。只是赵任宗给人一吓,从死到生走了一遭,骇然之余,心念早已溃堤,一时只知全力奔逃,更不敢再回头多看一眼。远处溪水淙淙,伴随着赵任宗的惨叫,听来倍觉怪异。看这位都尉受惊过度,可别失心疯了。※※※嘎地一声轻响,石门再次开启,这回门里行出一名老僧,这人面容枯槁,神色凛然,正是天绝到来。他陡由黑暗现身,日光如此刺目,双眼自也刺痛难当。不过天绝毕竟是饱经历练的武学宗师,当此险地,索性闭紧双眼,一股气劲向前扑出,方圆五尺内无人可近。此刻便有大批人马手持弓箭暗算,自也奈他不得。天绝目不能视,却知身边有人隐伏,他闭紧双眼,冷冷地道:“你来迟了。依着约定,你两日前便该抵达。”尽管面对四大宗师,那人语气依旧无畏无惧,只听他微微一笑,道:“大师可别强人所难。朝廷有点事,公务繁忙,一时走不开。”天绝哼了一声,道:“当年让你下山,老僧可不曾出言推托。”那人听他提起往事,笑声登时转为阴沉,回话道:“当年是当年,现下是现下,何必混为一谈?大师,明人不说暗话,宁不凡把人交给了你,等于是交给了我,你不必拿我当外人看。”陡听此言,天绝僧双目睁开,眼中神光暴射而出,赫然间,便已见了地下流着一行血迹,他怒气勃发,森然便道:“你又杀人了!当年放你下山,你发过什么誓来着?”那人耸了耸肩,笑道:“是他自己撞上去的,怪我不得。”天绝僧面色阴森,当下推门肃客,示意来人进入洞中。那人见天绝脚步迟迟不动,登时微笑道:“大师啊,便你这般高的武功,也怕走在我前头么?”天绝并不受激,合十便道:“潜龙凤羽,单凭智谋便能杀……”那个“人”字一出,左手已扣住那人手腕,手法快若闪电。他语气转为平淡,说道:“阁下便算手无缚鸡之力,老衲也无半分轻视之意。”说话间掌中加劲,似要狠狠惩戒那人一番。那人却无惊慌之意,只听他淡淡笑道:“大师,我手腕上抹了毒药哦。”天绝身子一震,脸上闪过黑气,正要发动神功驱毒,那人又笑道:“骗你的。”天绝大怒欲狂,脸色更如山神凝重,森然便道:“潜龙……潜龙……为何你父子都是聪明绝顶之人……”他顿了顿,将那人脉门放开,眼中杀气却更浓洌:“性子却相差如此之远?”那人轻松如故,只听他森然一笑,反问道:“你说呢?”袍袖一拂,径自跨门入洞,极见潇洒之能事。天绝深深吸了口气,他不再打话,便也行入门中,跟着反手轻推,掩上了石门。[记住网址.三五中文网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