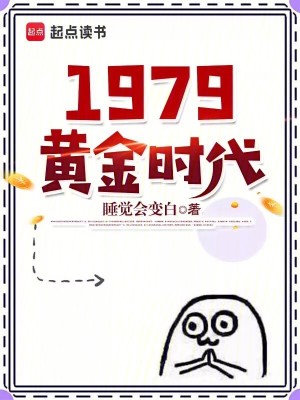第476章 饮酒思乡
在湾仔有一条杜老志道。
在杜老志道,有一家杜老志舞厅。
开了几十年,声名赫赫,是香港最大的销金窟之一,白天不开门,晚上营业,艳光四射的门面映照着各式豪车,连门口那对石狮子都不是干净的。
“滴滴!”
一辆平治开了过来,泊车小弟殷勤的迎上去,黄霑大方的甩出一张纸币。
另一个小弟也期待着,结果一辆万事得开过来了,他一咧嘴,来这的不是美国车就是德国车,要么是英国车,你开一日本车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!
但既然是客人,就得招待。
小弟想帮忙开车门,一只大手伸出来,啪的扣住他腕子,像老虎钳子一样生疼,里面有人问:“你做什么?”
“泊车啊!还能做什么?”
“不必!”
“喂,你懂不懂规矩?”
小弟嚷了一声,顺着这只手往里看,是一条跟自己腿差不多粗的胳膊,一个矮壮矮壮像熊似的男人盯着自己,他没来由心下发毛,下一句卡在喉咙里不敢吭声。
“这是我朋友,没事没事!”
黄霑笑呵呵的过来,也甩出一张小费,小弟哼了声:“我给霑伯面子啊,开万事得有什么好神气?”
“您认识他?”
小莫先下来,给陈奇开车门,陈奇这才下了车询问。
“我常来这里,自然认识,他们是泊车小弟,靠这个吃饭的,你不让他们泊就赚不到钱喽。”
“哦,我的车不能被人动。”
“入乡随俗嘛!”
“入乡随俗……”
陈奇笑了笑,道:“您怕黑社会?”
“……”
黄霑一噎,以他的才智却应对不了,真话最伤人。
说晚上一起喝酒,他故意选了杜老志舞厅,想看看对方的反应,结果开局就落了威风。他狂放不羁,但又不是傻子,香港谁愿意招惹社团?
俩人往里走,小杨留在车内,小莫跟着。
门口站着青春靓丽的迎宾小姐,还有个白人,一看就是俄罗斯那边的,操着一口还算流利的粤语:“欢迎光临!”
进了大门,则是一个迎宾台。
再往里走,有服务生专门伺候,见了黄霑跟见了亲爹似的:“霑伯,好久没来光顾了,这位先生是你朋友啊?哇,又威风又有气质,一定是位大老板!”
“哈哈,他可不是老板,你们好生招待就是了!”
进了舞厅,黄霑一下子如鱼得水,不时与路过的小姐和妈妈桑打招呼。他本来就是个老色批,对风月场所如数家珍,还出过一部纪录片,介绍了香港的嫖妓史。
“杜老志当年开业,当时没有酒牌的,只有茶和瓜子,小姐在场内卖香口胶和鱿鱼丝。70年代就火了,点一首歌要8美金,一顿酒能花掉普通人几个月工资。”
他边走边给陈奇讲解:“现在生意更好,有200个公关小姐,就是舞女喽!对面有家花档看见了吧,杜老志每天从那里订花都要2万块。”
“那是香港最大的舞厅了?”陈奇问。
“最大的之一,你看这地方,5000多尺啊!”服务生满脸自豪。
“400多平米,还没有我在京城的院子大。”
“……”
服务生也一噎,问:“霑伯,这位是大陆的客人?”
说话间到了座位,软皮沙发围着一张桌子,黄霑大大咧咧坐下,笑道:“是啊,叫你们最靓的小姐过来,给我们大陆同胞看看!”
很快,六个公关小姐来了,花枝招展的站成一排,任君挑选。
“今天我买单,不必客气!”
黄霑有意看他如何做,这种文化人大多有个毛病:喜欢用自己的才智和学问戏谑、调侃对方,从而获得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
陈奇虽然喜欢黄霑,却不惯着,摇摇头:“您随意,我不必了。”
“怎么,怕违反党规啊?”
黄霑好像找到了突破口,笑道:“你在香港怕什么,大陆又不知道,玩一玩逢场作戏嘛!还是说你都不喜欢,OK,换一批!”
“霑叔!”
陈奇一伸手,搭住他胳膊,笑道:“您怕黑社会,我怕党纪国法,总归还是我好一点,哪里来的优越感呢?我叫您一声霑叔是尊敬您,这种做派没意思的,聊聊天吧?”
每个人都是综合体。
黄霑有家国情怀,也不妨碍他的种种缺点。
正如他自己在文章里写到:“虽然明知自己中国人身份,但对外地同胞,总有些未必言宣,却其实存在的歧视。这歧视不一定很深,但有歧视倒无可否认。”
香港人不歧视大陆人,是不可能的,2024年还特娘歧视呢!
黄霑没接触过陈奇,第一次见面,总会带点惯有的习气,闻言一愣,有些悻悻的让小姐们下去,却也爽快:“是我下乘了,自罚三杯!”
喝的是洋酒。
洋酒的三杯,跟啤酒、白酒不一样,每杯就倒那么一小点。
他三杯酒下肚,精气神明显高涨,一颗硕大的鼻子仿佛在抖动,牙齿也很大,咧开嘴像要吃人,道:“你说给我带了好酒,好酒在哪里?”
“小莫!”
陈奇唤了声,小莫把手里的箱子递过来。
“这大半年,我把各地的名酒都给您送遍了,北至黑龙江的北大仓、内蒙的马奶酒,东至江浙的女儿红、双沟洋河,山西的汾酒,陕西的西凤,西南的茅台五粮液,广东的石湾玉冰烧……实在没有什么可送的了,这是我私家珍藏……”
黄霑也很好奇,伸着脖子瞧。
只见陈奇砰砰拎了两瓶不起眼的绿玻璃瓶出来,商标都很旧了,说是打酱油的瓶子都有人信。
“咝!”
黄霑却倒吸了一口张国荣,眼睛发亮。
那俩破瓶子,一瓶是虎骨酒,一瓶是虎鞭酒。
“哈哈哈!我早该请你饮酒的,你懂男人心,不过两瓶太少了,两箱才够劲!”
“两箱?”
陈奇一副你在想屁吃的表情,道:“大陆现在也越来越少了,我是几年前存了一点,两瓶已经是忍痛割爱。等以后禁止了,这两瓶酒堪称绝版,收藏都有价值啊!”
他确实肉痛,一下子少了20分之一。
黄霑却挺乐呵,当即收下,这东西在香港也少,还难买正宗的。
到此为止,二人才算铺垫完毕,互相觉得可以沟通。
黄霑什么酒都喝,在这里自然喝人头马,陈奇上辈子也喝,丝毫不怵,问:“霑叔,我们的春节晚会您觉得怎么样?”
“很棒啊,出乎意料的好,你今年还搞么?”
“搞啊!观众反响太过热烈,不搞会死人的,您在香港根本想象不到那首《我的中国心》有多火,回一趟大陆就知道了。其实大陆现在……”
“诶,不要讲这些,我请你饮酒,就是觉得你不会给我上课。”
黄霑一摆手。
“好,那我不讲。”
陈奇笑笑,又道:“听说您是广州西关人,几时来的香港?”
“8岁喽!”
“您家住在十六甫东四巷,隔壁是傅老榕。”
“不错!我父亲当年白手起家,从轮渡上的小工做起一直干到工头,在广州置办了房产。我父亲与傅老榕的关系很好,后来他去澳门,还混成了赌王。”
傅老榕30年代去澳门,经营博彩业二十多年,是何鸿燊的师傅。
黄霑似笑非笑,道:“你功课做的很足,调查我很全面,还有什么想讲的?”
“我只是想告诉您一声,您家的房子很好,由于找不到房主,现由房管局代管,租给了一家国营企业做幼儿园使用,有几十个小孩子,每天都很快乐的在那里上学玩耍。
如果您想看看,我下次给您带几张照片。
还有租用的租金,如果您愿意,可以补签一个协议,租金按季度补还给您。或者您不愿意租了,也可以,我们沟通当地,把房子腾出来。”
“……”
黄霑本想听听他要讲什么,一下子就不作声了,看了看他,喝了口酒,自己父亲已去世了,母亲还活着呢,广州还有个二姐做人民教师,还是个党员,各种关系割舍不断的。
他又喝了口酒:“我与我家人商议一下吧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