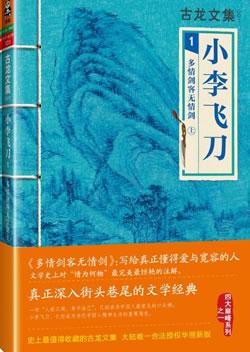李寻欢又走出了几步,才缓缓停下,望着长街尽头一株孤独的枯树,痴痴地出了半天神,终于缓缓转回身,道:“好,我回去,你……你多多保重。”虬髯大汉点了点头,嗄声道:“少爷你自己也多多保重了。”他不再去望李寻欢,低着头自李寻欢身旁走过去,走出了十几步,忽又停下,转身道:“少爷你若是没有别的事,还是在这里多住些时候吧,无论如何,龙大爷的确是条好汉子,好朋友。”李寻欢仰天叹道:“得友能如龙啸云,夫复何恨!”虬髯大汉道:“少爷若已决定住下,说不定我很快就会回来找少爷的。”李寻欢笑了笑,道:“也许我会住下来的,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”他虽然在笑着,但笑得却是那么凄凉。虬髯大汉骤然转身,咬紧牙关大步冲了出去。天色渐明,雪意也越来越浓了。死灰色的穹苍,沉重得似将压了下来,可是虬髯大汉的心情却比这天色更灰暗,更沉重。无论他是为了什么而逃的,总之他现在又要开始过那无穷无尽的逃亡生活了.他已和李寻欢逃亡了十年,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逃亡生活的痛苦,那就像一场噩梦,却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候。但在那十年中,至少还有李寻欢和他在一起,他还有个人可以照顾,他的心情至少还有寄托。而现在,他却已完全孤独。他若是个懦夫,也许反而不会逃,因为他知道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比这种孤独的逃亡生活更痛苦。甚至连死亡都没有!那种绝望的孤独,实在能逼得人发疯。但他却非逃不可,眼看李寻欢似乎又可以安定下来,他只有走,他无论忍受任何痛苦也不能连累了李寻欢。现在,他本该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今后的去向,但他却不敢让自己静下来,他要往人最多的地方走。他茫无目的地走着,也不知走了多远,忽然发现已到了一个菜场里,他自己也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他这一生中,也不知到过多少种地方,上至世家大族的私邸,下至贩夫走卒住的大杂院,上至千金小姐的闺阁,下至花几十枚大钱就可以住一夜的土嫖馆,最冷的地方他到过可以把人鼻子都冻掉的黑龙江,最热的地方他到过把鸡蛋放在地上就可以烤熟的吐鲁蕃。他曾在泰山绝顶看过日出,也曾在无人的海滩上看过日落,他曾经被钱塘的飞潮打得全身湿透,也曾被大漠上的烈日晒得嘴唇干裂,他甚至在荒山中和还未开化的蛮人一齐吃过血淋淋的生肉。可是到菜场来,这倒还是他平生第一次经历。在冬天的早上,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比菜场人更多,更热闹的地方了,无论谁走到这里都再也不会觉得孤独寂寞。这里有抱着孩子的妇人,带着拐杖的老妪,满身油腻的厨子,满头桂花油香气的俏丫头……各式各样不同的人,都提着菜篮在他身旁挤来挤去,和卖菜的村妇、卖肉的屠夫为了一文钱争得面红耳赤。空气里充满了鱼肉的腥气,炸油条的油气,大白菜的泥土气,还有鸡鸭身上发出的那种说不出的骚臭气。没有到过菜场的人,永远也不会想到这许多种气味混合到一起时是什么味道,无论谁到了这里,用不着多久,鼻子就会麻木了。但虬髯大汉的心情却已开朗了许多,因为,这些气味,这些声音,都是鲜明而生动的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!—世上也许有许多不想活的人,有人跳楼,有人上吊,有人割脖子,也有人吞耗子药……但却绝没有人会在菜场里自杀的,是不是?在这里,虬髯大汉几乎已将江湖中那些血腥的仇杀全都忘了,他正想花两个铜板买个煎饼尝尝。突听前面一人直着嗓子吼道:“卖肉卖肉,卖新鲜的肉……”这声音刚响起来,就被一阵惊呼声打断了。接着,前面的人都惊呼着向后面退了回来,大人们一个脸如死灰,孩子个更是哭得上气接不了下气。后面的人纷纷在问道:“什么事?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的?”从前面逃回来的人喘息着道:“有个人在卖肉。”后面的人笑了,道:“这里至少有几十个人在卖肉,有什么好害怕的?”前面的人喘息着气道:“但这人卖的肉却不同,他卖的是人肉!”菜场里竟然有人卖人肉,这实在连虬髯大汉都吃了一惊。只见四面的人越挤越多,大家心里虽害怕,但还是想瞧个究竟——有许多女人到菜场去,本就并非完全是为了买菜,也是为了去和别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磕磕牙,聊聊天,交换交换彼此家里的秘密,瞧瞧别人的热闹。有这种怪事发生,谁还肯走呢?虬髯大汉皱了皱眉,分开人丛走过去。他脸上也立刻变了颜色,看来竟似比任何人都吃惊。在菜场里,肉案总是在比较干净的一角,那些手里拿着刀的屠夫,脸上也总是带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。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自己卖的才是“真货”,到这里来的主头总比那些只买青菜豆腐的人“高尚”些。这种情况正好像“正工青衣”永远瞧不起花旦,“红倌人”永远瞧不起土娼,却忘了自己“出卖”的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此刻那些平日趾高气扬的屠夫们,也已都被骇得矮了半截,一个个都缩着脖子,直着眼睛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最大的一家肉案旁还悬着招牌,上面写着:“黄牛口羊,现杀现卖。”肉案后面站着个又高又大又胖的独眼妇人,手里拿着柄车轮般大小的剁骨刀,满脸都是横肉,一条刀疤自带着黑眼罩的右眼角直划到嘴角,不笑时看来也仿佛带着三分诡秘的狞笑,看来活像是凶神下凡,哪里像是个女人。肉案上摆着的既非黄牛,也非口羊,那是个人!活生生的人!这人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,露出了一身苍白得可怜的皮肤,一条条肋骨,不停地发着抖,用两条枯瘦的手臂抱着头,缩着头伏在肉案上,除了皮包着骨头之外,简直连一两肉都没有。独眼妇人左手扼住了他的脖子,右手高举着剁骨刀,独眼里凶光闪闪,充满了怨毒之意,也充满了杀机。虬髯大汉见到了她,就好像忽然见到了个活鬼似的,面上立刻变得惨无人色,一瞬间便已汗透重衣。独眼妇人见到了他,脸上的刀疤忽然变得血也似的赤红,狠狠瞪了他几眼,才狞笑着道:“大爷可是来买肉的么?”虬髯大汉似已呆住了,全未听到她在说什么。独眼妇人格格笑道:“货卖识家,我早就知道这块肥羊肉除了大爷你之外,别人绝不会买,所以我早就在这里等着大爷你来了。”虬髯大汉这才长长叹出口气,苦笑道:“多年不见,大嫂你何苦……”独眼妇人忽然“呸”的一声,一口痰弹丸似的飞了出去,不偏不倚,正吐在虬髯大汉的脸上。虬髯大汉既没有闪避,也没有伸手去擦,反而垂下了头。独眼妇人已怒吼着道:“大嫂?谁是你这卖友求荣的畜生的大嫂!你若敢再叫我一声大嫂,我就先把你舌头割下来。”虬髯大汉脸上阵青阵白,竟不敢还嘴。独跟妇人冷笑着道:“你出卖了翁天迸,这些年来想必已大富大贵,发了大财的人,难道连几斤肉都舍不得买吗?”她忽然一把揪起了肉案上那人的头发,狞笑道:“你若不买,我只好将他剁了喂狗!”虬髯大汉抬头瞧了一眼,失声道:“梅二先生,是你?”肉案上那人似已骇得完全麻木,只是直着眼发呆,口水不停地沿着嘴角往下流,哪里还说得出话来。虬髯大汉见到他如此模样,心里也不禁为之惨然,嗄声道:“梅二先生,你怎地落到……”独眼妇人怒喝道:“废话少说,我只问你是买,还是不买?”虬髯大汉长长吸了口气,苦笑道:“却不知你要如何卖法?”独眼妇人道:“这就要看你买多少了,一斤有一斤的价钱,十斤有十斤的价钱。”她手里的剁骨刀忽然一扬,“刷”地砍下。只听‘夺’的一声,车轮般大的剁骨刀已没人了桌子一半,只要再偏半寸,梅二先生的脑袋只怕就要搬家。独眼妇人瞪着眼一字字道:“你若要买一斤,就用你的一斤肉来换,我一刀下去,保险也是一斤,绝不会短了你一分一钱!”虬髯大汉嗄声道:“我若要买他整个人呢?”独眼妇人厉声道:“你若要买他整个人,你就得跟着我走!”虬髯大汉咬了咬牙,道:“好,我跟你走!”独眼妇人又瞪了他半晌,狞笑道:“你乖乖的跟着我走,就算作聪明,我找了你十七年八个月才将你找到,难道还会再让你跑了么?”虬髯大汉仰天长叹了一声,道:“我既已被你找到,也就不打算再走了!”山麓下的坟堆旁,有间小小的木屋,也不知是哪家看坟人的住处,在这苦寒严冬中,连荒坟中的孤鬼只怕都已被冷得藏在棺材里不敢出来,看坟的人自然更不知已躲到哪里去了。屋檐下挂着一条条冰柱,冷风自木隙中吹进去,冷得就像是刀,在这种天气里,实在谁也无法在这屋里呆半个时辰。但此刻,却有个人已在这屋里逗留了很久。屋子里有个破木桌,桌上摆着个黑黝黝的坛子。这人就盘膝坐在地上,痴痴地望着这坛子在出神。他穿着件破棉袄,戴着顶破毡帽,腰带里插着柄斧头,屋角里还摆着半担柴,看来显然是个樵夫。但他黑黝黝的一张脸,颧骨高耸,浓眉阔口,眼睛更是闪闪生光,看来一点也不像樵夫了。这时他眼睛里也充满了悲愤怨恨之色,痴痴的也不知在想什么,地上早已结了冰,他似已全不觉得冷。过了半晌,木屋外忽然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。这樵夫的手立刻握住了斧柄,沉声道:“谁?”木屋外传人了那独眼妇人沙哑而凌厉的语声,道:“是我!”樵夫神情立刻紧张起来,嗄声道:“人是不是在城里?”独眼妇人道:“老乌龟的消息的确可靠,我已经将人带回来了!”樵夫耸然长身而起,拉开了门,独眼妇人已带着那虬髯大汉走了进来,两人身上都落满了雪花。外面又在下雪了。樵夫狠狠地瞧着虬髯大汉,目中似已冒出火来。虬髯大汉却始终垂着头,也不说话。过了半晌,那樵夫忽然转过身,“噗地”跪了下去,目中早已热泪盈眶,久久无法站起。忽然间,门外又有一阵脚步声传来。独眼妇人沉声道:“什么人?”门外一个破锣般的声音道:“是老七和我。”语声中,已有两个人推门走了进来。这两人一个是满脸麻子的大汉,肩上担着大担的菜,另一人长得瘦.瘦小小,却是个卖臭豆干的。